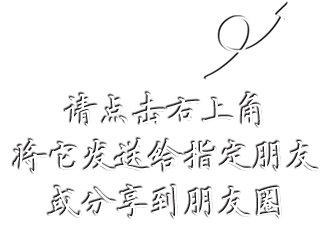■《艺术与物性》,巫鸿编著,上海书画出版社2023年5月第1版。

■大汶口文化玉斧。

■江苏武进寺墩良渚文化“玉敛葬”。

■带有“族徽”的良渚玉斧,反山大墓出土。

■商代白陶器,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藏

蔡国强,火药爆破行为表演,卡塞尔文献展,1992
新书《艺术与物性》,引入观看艺术的第三视角“物性”
日前,新书《艺术与物性》由上海书画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是由著名美术史家、艺评家、策展人巫鸿主持编著的“中国材质艺术”丛书第一辑。丛书以专题分析方式,针对中国艺术中的各种材质,展示不同材料在中国美术史中的重要性,探索这些材料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宗教、政治、性别和思想上的含义。
在本辑《艺术与物性》中,巫鸿与海外学者林伟正、刘礼红、黄爱伦的五篇文章,从史前时代到当代艺术,涵盖了中国美术史的全过程。内容上,它们分别聚焦于史前玉器和特殊陶器、中古时期以不同材质制作的佛像、物质文化与视觉文化中对玻璃的使用、瓷的材质性和清代皇家的瓷器制作,以及当代中国艺术中的“材质艺术”潮流。
巫鸿认为,材质不仅是艺术品的物质基础,也是艺术精神表达的重要媒介。他在“图像”与“物件”的基础上,提出了第三视角——“物性”。
■收藏周刊记者 潘玮倩
1
什么是“物性”?先说“图像”与“物件”。
欣赏和研究艺术品的角度有多种。最常用的角度是“图像”,“图像”是人类创造的视觉再现。近年流行的一种角度,是将视点从“图像”转移到“物件”上,不但研究其制作、构成、功能,而且追究其流通、变异、毁坏以及变化中的意义,也就是“物之生命”。
巫鸿则提出了第三个研究和理解艺术品的角度——“物性”。在书的前言,他解释道,“物性”包含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一是用以制作艺术品和建筑物的物质材料(material);二是材料在意识形态和审美层次上的“质量”(quality)。“材质”一词综合了这两个方面,同时指涉着艺术品的“材”和“质”。
比起“图像”和“物件”,“物性”和“材质”探究了艺术品的更基本且广泛的创造意义——包含了物质和精神两个维度,既引导我们探究艺术创作对物质材料的使用方式,又促使我们思考材料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宗教、政治、性别和思想含义。
由于古今中外的任何艺术品都具有材质性,这一观念也超越了时代和地区的限制。
“材质”与“艺术”的关系是什么?巫鸿解释道:“这些材料中,一些来源于自然的稀有物质,通过人为的选择和加工显示出特殊的材质特性;另一些则是人类的发明创造,以技术手段把自然物质改造为具有特殊性格的材质(‘在中国历史上,这一转化过程发生于新石器时代’,编者引述注)。两种情况都显示出把材料转化为材质的过程,因此都具有艺术创造的内涵。”
比如,如果我们希望理解中国艺术的产生和早期发展,我们就必须了解“社会概念和政治原则”如何通过礼器转化为视觉形式,以及“材质”在这种转化中起到的作用。
2
从对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出现的玉石器和特殊陶器进行的简要分析入手,巫鸿在题为《“材质”与中国艺术的起源》的首篇文章,探讨了材质概念的最初发生,并由此追溯中国艺术的萌生。
在笔者看来,精心雕琢的玉器和具有特殊材质的“蛋壳陶”,标志了一种特殊审美的产生,用来制作它们的物质并不是实用意义上的材料,而是具有社会、政治和审美意义的特殊材质,由此开启了中国美术中的一个漫长传统。
书中写道,中国新石器时期开始于公元前7000年之前,持续了大约五千年之久。在这个巨大的时间跨度中,人类的创造物逐渐“被看作高于自然的给予。随之出现的是社会财富的积累、贫富之间的分化以及特权观念的形成,均由大量考古材料得到证明。所有这些发展都导致一些‘特殊物品’的产生,集中体现为特别设计制作的陶器和玉石雕刻”。
美石为玉,漂亮的石头逐渐被先民们划定为“玉”。这一由石到玉的演进,已被多年的考古工作证实:“打制和磨制的石器是旧石器时代以来漫长时期中的主要生产工具,但以美丽坚硬的玉料制作的器物只集中出现在新石器晚期。”
与石器相比,史前玉器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促进生产,而在于“藏礼”,以其特殊的材质和视觉效应体现社会与宗教性能。
巫鸿引用了这类作品的早期代表——出现于大汶口文化中的玉斧。“由于玉石的超高硬度,其切割和造型不能依靠制造石器的方法,而需要以解玉砂为介质费工费力地琢制研磨。即使如大汶口玉斧这样一件造型简单的制品,也要经过选料、粗胚、成型、 打磨、钻孔、抛光等工序,至少需要数月才能完成。”
我们因此必须发问,是什么原因使大汶口人制造了这种外形上类似石器、但却需要花费百倍人力的玉斧?
巫鸿认为:“它看似普通物件,但材料却不寻常。对于深谙雕琢玉石之难的当时人而言,这意味着在这个小小物件里凝聚着惊人的劳力和技术知识,它也由此象征着其所有者控制与浪费大量人力和技术资源的能力。通过它的简洁形状和珍贵材质,玉斧由此成为‘权力’的实物象征。”
一旦“材质艺术”脱离了实用性器物,它也就摆脱了实用性器物的规律,而跟随自己的逻辑发展。大汶口文化只是制作玉器的诸多史前文化中的一个。根据考古学家的观察,在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之间,中国大陆东部地区形成了北(红山系)、中(大汶口、龙山系)、南(良渚系)三大玉器文化系统。“每个地区里的玉器都有不同特点,但都属于‘材质艺术’的基本范畴。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玉雕代表了大汶口玉器的进一步发展。”
3
林伟正在其《万佛:中国中古佛像材质的思考》一文中,提出自佛教美术产生伊始,用以制作佛像的材料就已经多种多样,并随着时间增多,形成不同的造像门类。每种材料都有特定的物质属性、相应的工艺和制作方式,决定了佛像的呈现方式及其相应的使用模式。不同材料的选择既在于地区的自然条件以及材料的经济和文化价值,但同时也成为显示佛像神圣性的视觉表现方式,因此获得了艺术中的“材质”意义。他认为只有将这种意义置入造像的宗教体系中去探究其概念和功能,才有可能更完整地窥探中国中古佛像的宗教和艺术价值。
刘礼红的《玻璃之灵晕:兼论容器的物质氛围》,追溯了玻璃这种人造物质在世界各地和不同时期中的使用,探讨了它的“质”与“名”的关联和混淆、玻璃在“天然”与“人工”之间的模糊存在,以及它在中国物质文化和视觉文化中的多重意义,包括在一波一波的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和意义。“灵晕”的概念进而引导她发掘玻璃的现代性:这种材质在现代社会中的广泛使用引起对形、质和环境关系的重新思考。总括的看,玻璃这种古老的材质一直在跨文化、跨地理和跨时间的过程中获得技术的发展和物质的演变。不同历史时期和地点对它的含义不断地“再建构”,在时空交织之中激发出新的感知经验。
黄爱伦的《转化的艺术:清代瓷器中窑变釉的再造》,围绕“窑变”现象和“火气”概念对瓷的材质性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文章以文献、实物和技术分析为基础重新检验了窑变的实践、概念和历史,并围绕清代的钧瓷考察了对窑变的再造,以及由窑变生成的变化无定的釉彩对皇室赞助人的意义。整篇文章的核心观念是“转化”。用作者的话说:“的确,还有什么方式比将原始、野生状态的泥土资源转化为人工制造的瓷器能更好地体现变化呢?作为一种如此精致、光滑、耐用和通用的材质,瓷只能在作坊中经过一系列转化来制造,而不能在自然界中寻获。”
最后,巫鸿的《当代中国艺术中的“材质艺术”》,从一个新的角度回顾了当代中国艺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一个重要方面。“材质艺术”指的是有意以特殊材料创作的大量作品。这些材料被艺术家选择和采用,赋予能动性,成为他们长时期内的创作方式,用于绘画、雕塑、装置、行为等各种艺术门类。如此使用的材料因此超越了艺术形式的限制,而且在这些形式之间扮演着“超级介质”(super-agents)的角色。
(本版图文资料由上海书画出版社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