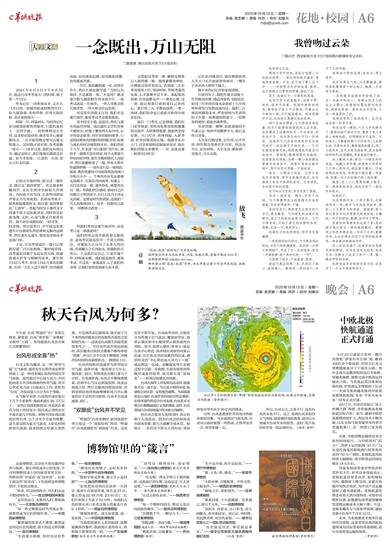□杨兴杰 西安邮电大学2022级网络与新媒体专业本科
我曾吻过云朵。
那孩子手中的线,是我与喧嚣人间的最后纽带。一阵任性的南风袭来,那线猝然崩断。于是,我开始了第二次飞行——一次短暂而失控的坠落,最终,这片梧桐以它繁茂的臂膀,接住了我。
夏日,我被囚于一片绿色的深海。
我的竹骨卡在枝桠间,动弹不得。起初,我并不寂寞。我拥有绝佳的视角:看那孩子每日午后跑来,仰着沁出汗珠的小脸,巴巴地望着我。我多想俯冲下去,用我的羽翼拂过他的发梢。
树叶是如此稠密,它们将我层层包裹,阳光只能费劲地挤进来几点光斑。我仿佛成了这棵树的另一片古怪的、彩色的叶子。我与真正的叶子们一同呼吸。我感受它们在最炽热的阳光里如何进行一场寂静无声的狂欢——它们贪婪地吞咽光热,将绿意燃烧到最浓烈的地步。雷雨夜,整棵树剧烈地摇晃,我紧紧抓住树枝,仿佛一艘小舟颠簸在墨绿色的海浪中。我聆听着雨点敲打树叶,那声响宏大得像一万面战鼓。
我与一只蝉成了邻居。它终日在我身旁嘶鸣,那声音粗糙而热烈,是专属夏日的永不降调的宣言。它告诉我,生命就当如此喧嚣。
但不知从何时起,宣言变成了挽歌。
先是一场凉雨。随后,风变了味道。它不再携带泥土的蒸腾与花朵的甜腻,而是变得清冽、干燥。
我的邻居们,那些曾无比热烈的叶子们,最先察觉。它们绿色的血液开始褪却,染上了疲惫的金黄与赤红。它们不再絮语,开始了漫长的安静的告别。那蝉,在某一天,戛然而止。
我感到卡住我的树枝,前所未有地僵硬。
一阵更萧瑟的风穿过,它不再试图托起我,而是无情地推搡着。我身旁一片硕大的梧桐叶,完成了它一生的使命,发出一声极轻微、极干爽的叹息——“咔”。
它脱离了枝头,开始盘旋、堕落。
就在它离去的那一刻,风找到了缺口,猛地灌入。缠绕我一夏的枝叶,松开了它的怀抱。
我那场中断的坠落,在秋天,得以续写。
我没有再次飞起,只是飘摇着,最终落在覆满落叶的土地上,触感一片冰凉与柔软。
一双粗糙而温暖的手拾起了我。是一位散步的老人。他拂去我身上的尘土与露水,眯着眼打量我褪色的彩绘、残破的绢面。眼神里没有惊奇,只有一种温柔的了然。
他将我带到了他的院子。我不是这里唯一的异乡客。
院里也有一棵树,叶子几乎快掉光了,黝黑的枝干伸向天空,像极了老人手背上清晰脉络。但那棵树并不哀伤。它的枝头,飞舞着代替叶子的东西:几条鲜红的、明黄的丝巾,像被捕获的霞光;两三只纸风车,在风里欢快地旋转,发出细碎的哔啎声;半张糖纸,亮晶晶地闪着光。
老人搬来木梯,取出一个褪色的针线盒。他戴上老花镜,就着秋日明亮却已不灼人的阳光,将我置于膝头。仔细检视我的伤处,那神情不像打量一件废物,倒像一位大夫在聆听病人的往事。
缝罢,老人小心翼翼地攀上梯子,用一根柔软的布条,将我系在了一根向阳的枝头。
风渐起了。
先是那纸风车,三两片翼子,迟疑地咯吱一转,继而飞快地旋动起来,搅起一小片看不见的涡流。紧接着,那几条红黄丝巾的末梢被风轻轻拎起,与糖纸一同开始舒卷、飘拂,如同有了呼吸。
系着我的那根布条也紧了紧,我的翅羽随之发出一阵轻微的颤抖。整棵树上的色彩便在这一刻活了过来,簌簌作响,与远处清冷天空下光秃的枝条形成一种寂寥而执拗的对峙。
老人站在屋檐下,灰布衫的衣角被风轻轻拂动。风吹乱他花白的发,他亦不动,仿佛自己也成了院中一景,像一棵会呼吸的老树。
我终究没有回到孩子的天空,但我有了一个永不凋落的秋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