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药师 很偶然地找到了自己的家谱,就像一条小溪孤零零地流淌了好久,不经意间转见了自己源头处的大河。那感觉又亲切又陌生,又激动又荒谬。于是关在家里研究十八代祖宗。结果研究得越多,感触也就越复杂。 我家家谱记录的堂号是培远堂,又称长沙纯化袁氏,能清楚上溯到元朝末年,将近六百六十年的清晰传承,厚重得像一本出土文物。家谱是1921年最后一次修订的,我望着它,它望着我,寂静无声里彼此都有了笑容,那种血脉相通却久别重逢后的温暖和松弛,来得并不汹涌,但熨帖而真实。 很幸运地在旧谱的编委上看到曾爷爷的名讳,还有我爷爷的名字。但是这一群人,我其实一个都没见过,连爷爷也只见过遗像。看着那一小格一小格的人名,我知道没有他们就没有我,可我怎么也不能把他们拼成任何图像,我只能望着电脑上族兄发来的发黄的纸质照片走神,那都是至亲家人啊!可是还没有手边的一杯热茶来得立体和真实。 我家祠堂曾经制式挺大,理所当然早就被砸光了,于是这几行繁体字,几个小竖方格,里面就装着一个亲人一生。看家谱这种事,其实最能悟到性起缘空。你前不见古人,后也没把握能有几个来者。它那么清楚地提醒你的出处和归途,你甚至不用多好的慧根,就能直接感触什么是真空妙有,能领悟到你只是侥幸拥有一段时空的尘埃,哪怕也曾仗剑走天涯,又或孤影照惊鸿,都拼不过族谱里最后的一场虚空。 我家没出过能进历史课本的顶级人物。只是在六百多年诗书未断过,文出过进士,武出过将军,当官的有过封疆大吏,经商的也曾富甲一方,连岳麓书院挂的“惟楚有才,于斯为盛”的牌子,也都扯得上点渊源。本来也觉得与有荣焉。但后来一琢磨,其实这个没什么好显摆的,上下五千年,谁没几个牛人亲戚?无非是懒得找或者找不到谱而已。 有族兄把家中数百个有功名和官职的先辈一一考证了出来,放在了网上激励后学,这自然劳苦功高意义深远。可更打动我的却是另外一件事:就这样一个长沙城里横跨几朝的郡望世族,其实很多族亲也不过是平平庸庸地过完这一生,大多数人都只是艰难地谋生,艰辛地养家,很多人只在族谱就留下了个名字,就忽然不见了。还有很多亲人名字并未成年,后面就跟着个“殁”或“夭”。同一个父系染色体,人数只要稍多一点,运气、际遇、能力和成就都判若云泥。一旦有亲人外出谋生,好容易就成了后会无期。这一类人其实比朱卷里的顶戴簪缨多了。我本来觉得大家族的离别,应该是十里相送,撕心裂肺的,看了家谱后才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人世间大多数离别其实都来得悄无声息。培远堂原来有十八大房,现在暂时能找回的只有十二房了。我想,家谱也好,年夜饭也罢,意义都在这吧。明知离别和疏远都是常态,所以才显得相聚和相亲那么珍贵。 我知道二十一世纪读家谱是一件多么无用的事,身边人很多都不在乎这个了,人间的悲欢并不相通,有人只觉得聒噪。后来也就释然地笑了,没用又如何?若上溯没有用,繁衍当然也值得怀疑,若繁衍都值得怀疑,那些成熟的人又在为什么忙碌?清明将近,我又想起已故的父亲,小时候带着我烧纸时,总要在火盆外边烧几张散纸,说是烧给无家可归的。我知道那也没有什么用,但我每次也都会烧上几张。
-
即时新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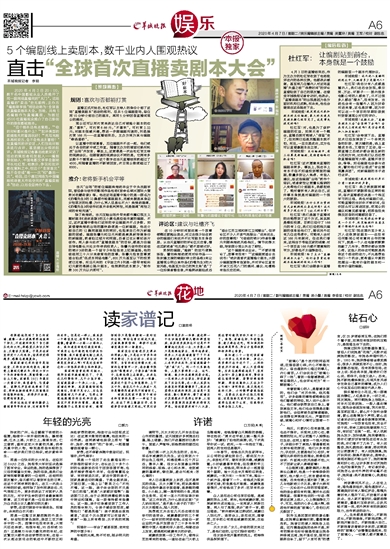
读家谱记
来源:羊城晚报
2020年04月07日
版次:A06
栏目:花地
作者:蓝药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