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慧谋 老家一带,宴席名堂多多,婚宴、满月宴、寿宴、入伙酒,等等。有时一家人,一天要赴好几家宴席,不去不行,礼尚往来,收过别人家礼数,总得要还的。更奇特的是,我都离开家乡三十余年了,有次回乡下,见到三弟家中一个请柬,顺手翻看一下,居然被邀赴宴的人是我,无语。 但你不能不说这是一份浓浓的亲情乡情,都这么多年了,还有人惦记着你。 唯独“街酒”没赴过,也是头一回知道有这么一回事。承志在电话里头说,老师,你不妨来感受一下。 休渔期的博贺渔港小镇,清静萧条了许多。码头上也不见了往时的喧嚣热闹,街巷上的行人更稀少。 席间承志说,下午四五点才热闹,整整一条东风街,都腾空下来摆街酒。 街酒的概念于我是模糊的。临近五点,我们由承志引路来到东风街,应该是小镇最中心的一条街道。进街口时承志说,这排旧房子的地方,过去小镇的人都叫它“中南海”。这个地方,当地人不止一次对我提过,现时看来,房子老旧得很,依然住着人家。许是在当年,这个地方的二层小楼建筑,称得上是小镇最好最奢华的?单门独户,二楼有飘台,门口外面有个不大的小院子。在那时小镇人的心目中,“中南海”也不外如此。 一条草绳居然可以阻止车辆和行人往来,横拉在东风街口,绳子一端挂着红纸写的告示牌:本街设街宴,禁止车辆进入,不便处多多包涵。 这就是民间法则,你得服从。行人进入内街,只得撑高草绳弯腰通过,除非你是侏儒,是刚学步的小孩。 街酒刚刚开始,整条东风街的街面都摆满台台凳凳,留出一条通道,方便行人和送菜的,基本是一户人家门口一张台,看来他们不怎么请外客,都是自家人的“街宴”而已。 承志带着我们一路走过去,总有人从席上站起来与他打招呼,由此可知,承志在小镇里人面很广。几乎打招呼的人,都邀请我们入席,热情十足。 街酒的菜统一由临时“厨房”派送,在街边转角处,搭起一大片棚顶,里面架起大炉灶,几位腰系围裙、脸戴口罩的“厨子”,一片繁忙,下菜起菜,接菜的一拨拨来,一拨拨把菜接走。整条东风街,处处都是拉着小平板车送菜人的身影。 这一幕,把我们看傻了。哪有这样吃法的?渔港小镇东风街有。上的都是大菜,整条油炸大红鱼,摆出花样的大虾,金黄爽口的炸肉卷,大盆里装着整只鸡的鸡汤,每道菜都让人觉得实在,不像有的酒店那样花样百出,吃得云里雾里。 场面也让人回到童年,像小时候过家家,一方饭桌摆在家门外,吃什么都见得着,家家户户如此。在东风街,感觉到一种久违的温馨。人间的幸福,再怎么的,也离不开人气、地气,离不开一种和睦相处的氛围,就像东风街的街酒一样。 我倒是好奇,虽是街酒,一点也不喧闹。他们围坐在圆台前,坐的都是清一色红色塑料凳,衬着灰色的街面,真是一道风景。没有人喧闹,没有人猜酒令,安静地吃。在沙栏街尾,见到一桌全是裸着上身气壮如牛的汉子,他们也出奇的安分,轻轻举杯,一圆桌悬浮半空的粗手臂,脖子一仰,一饮而尽。 这条沙栏小街,却有历史,上世纪60年代电影《山乡风云》在这条老旧的小街上拍了不少外景。 黄昏多好,一抹黄黄的斜阳,落在沙栏街口,街酒仍在继续……
-
即时新闻

街酒,人间的幸福
来源:羊城晚报
2025年03月11日
版次:A07
栏目:
分享到微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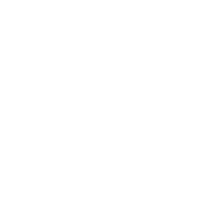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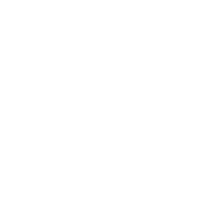
使用"扫一扫"即可将网页分享至朋友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