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敏 暨南园的记忆里,有一阵阵午后的雨,不约而至,遍地清凉;有一场场周末的电影,古今中外,异彩纷呈;有图书馆的灯光、教学楼的脚步声和西门外的小摊小贩……可最鲜活的部分,仍是和老师同学在一起的点点滴滴。其中,有关饶老师的部分,是欣喜与感恩。 准备考研的两三年间,我如饥似渴地查阅相关文献,“饶芃子”三个字逐渐成了关键词。读着所有能找到的饶先生的论文,发现其中不只是理论或观点,还有一种温暖的情意在其中,为什么?来到广州后,我才知道,作为潮汕学者,饶老师的学术选择关联着乡土潮汕。对于饶先生来说,研究华文文学,或许是以另一种方式回溯先辈走过的路,并将之纳入真理之塔中。 到暨大读书的头几年,我也只是远远地看着饶老师,以边缘的目光穿越层层叠叠的人群,感受源自中心的她的气息。她优雅得体的言谈举止、贴心热情的温暖问候,精彩独特的会议发言,都深深地吸引着我,然后,画面与文字相互补充,逐渐拼接出了一个完整的饶老师形象。 人到中年,渐渐明白,学者的真正使命,应如饶老师那样,以学问、人格,发出佛一般的生命之光,渡一切有缘人,无论时空的距离有多远。 2005年,我再次回到暨南园,攻读文艺学博士学位,饶老师还在上课。印象中的小班讨论课有两门,都是饶老师开的“海外华文文学”,或还有“比较诗学”,我都选了。在会议室里,人不多,我总是坐在饶老师对面,她的一切都入目入心,有小小的满足感。 讨论课上,我一向有自己的想法,但从不敢第一个发言,不过,饶老师的课会点名,不放过每一个人。记得有一次讨论白先勇的“永远的尹雪艳”,饶老师叫我发言了,我讲完后脸有点发烫,不敢抬头看她,觉得自己的观点和别的同学比,是有些离谱了。可听到的却是饶老师的赞美,她说:“很好,我们会将这一次讨论整理成一篇小文章,你的观点也要写进去”。 期末交了论文,我写的与《红楼梦》有关,饶老师看毕,在文学院的楼梯口与我有一段简短的对话。印象非常深刻。她先说“你会成为一个好学者的”,我窃喜;她接着说,“不过你还是《红楼梦》里大荒山的石头,需要雕琢历练”。 饶老师去年离开了我们,听闻这个消息,我很难过,可没有流泪,我知道她走得很安详。只是在后来的日子里,不时会想起一些关于她的细节,譬如在讨论班上,她就坐在我对面,点名要我发言……
-
即时新闻

她就坐在我对面
来源:羊城晚报
2025年03月13日
版次:A10
栏目:
分享到微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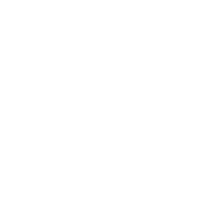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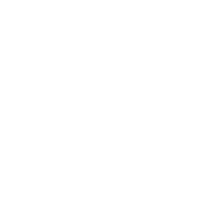
使用"扫一扫"即可将网页分享至朋友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