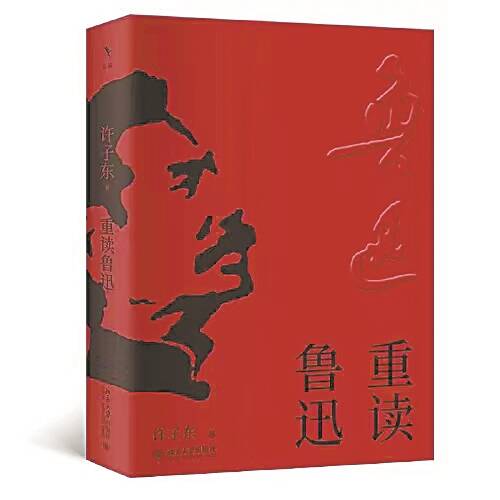
|
|
|
□许子东 《阿Q正传》到底是写“奴隶”革命还是“奴才”造反,曾经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学术界引发激烈争论。不过当时术语有所不同,“奴隶”说的是农民身份的阿Q,欺软怕硬自欺欺人的奴才心态则被称为“阿Q精神”,或者“阿Q主义”。 在特定的历史语境里,如何解说农民阿Q身上的“阿Q精神”或“阿Q主义”,成为一个难题。而且阿Q也不只是农民,他是雇农,没有任何生产数据生产工具,严格说来,是农村的无产者。怎么一个无产者,整天用虚幻想象排解屈辱,还要在现实中欺负弱势群体的小尼姑,还要再幻想中惩罚奴役同一阶级的小D并享用统治阶级的财产…… 50年代的学者们至少尝试了两个方法来解释以上困惑。一是赋予阿Q土谷祠之梦以斗争的正能量,强调奴隶必须革命;二是将阿Q的缺点跟优点区别开来,将奴隶身份与奴才心理切割。 前者的典型就是50年代鲁迅硏究的权威学者陈涌的《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陈涌认为鲁迅的《呐喊》《彷徨》“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的革命,反映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动力”,“鲁迅是现代中国在文学上第一个深刻地提出农民和其他被压迫群众的状况和他们的出路问题的作家,农民问题成了鲁迅注意的中心”,陈涌强调阿Q土谷祠里的梦“是鲁迅对于刚刚觉醒的农民的心理的典型的表现”,“它虽然混杂着农民的原始的报复性,但他终究认识了革命是暴力”,“毫不犹豫地要把地主阶级的私有财产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并且“破坏了统治了农民几千年的地主阶级的秩序和‘尊严’”,这都是表现了“本质上是农民革命的思想”。 第二种将阿Q的奴隶身份与奴才心理切割的方法,以何其芳、冯雪峰为代表。钱谷融在他的著名论文《论“文学是人学”》 中,摘引了几段相关评论:关于阿Q的典型性问题,已经争论了好几十年了,但是直到现在(1957年),大家的意见仍很分歧。何其芳同志一语中的地道出了这个问题的症结所在:“困难和矛盾主要在这里:阿Q是一个农民,但阿Q精神却是一个消极的可耻的现象。”许多理论家都想来解释这个矛盾,结果却都失败了。……为什么农民身上就不会有或者不能有消极的可耻的现象呢?是谁做过这样的规定的?……解放初期,不是就有许多人认为:说阿Q是一个农民,是一种农民的典型,是对我们勤劳英勇的农民的侮辱吗?……针对这种指责,理论家赶快声明说:阿Q只是个落后农民的典型,并不是一般农民的典型。同时,又特别强调阿Q的革命性,以期使他虽然有着那么多的缺点,终于还能配得上他光荣的农民身份…… 但把阿Q说成是落后农民的典型,问题依旧并没有解决。落后农民毕竟还是个农民,而且,他的落后决不是天生的,正是因为有了阿Q精神,才使他成为一个落后农民的。那么,他身上的阿Q精神,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冯雪峰是把阿Q和阿Q主义分开来看的。认为阿Q主义是属于封建统治阶级的东西,不过由《阿Q正传》的作者把它“寄植”在阿Q的身上罢了。 《阿Q正传》的评论史,某种意义上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一个缩影。文学形象阿Q身上的“奴隶性”,最具体地体现了鲁迅关于“奴隶”和“奴才” 这两个概念的长期思考。“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以后还万分喜欢。”这是鲁迅先生对我们(也包括对他自己)的一种提醒和警告。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重读鲁迅,也会发现鲁迅一生大部份作品都贯穿着一个主题: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