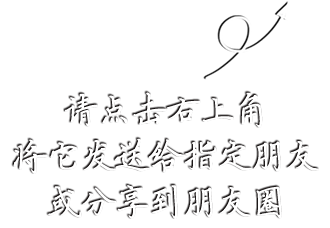□余冰如
世人谈茶,多观其色,其状,闻其香,品其味,却少听其声。
深夜人寂,是听茶的时分。
穿过深夜的耳朵,前人已有借茶听世间万物之声的趣味。元代的诗人卢挚留下“梦过煮茶岩下听,石泉呜咽松风冷”的诗句,也有煮茶听涛声,煮茶听泉之说。当然,这些听趣,多要在野外泉边、风起松林之处,才得几番品茗的野趣。但终究只是借品茗之闲,听世间之音,却未能真正简单地去倾听茶的声音。
几百年前日本茶人能阿弥说:“从茶炉发出的响声中去想象松鸣。”这是从水沸“噗噗”的响声中体会到的野趣。宋徽宗赵佶在《大观茶论》中谈到,烧水要烧到水面上“咕嘟咕嘟”连续泛出鱼蟹目一样的小气泡才行。能阿弥说到的松鸣声,大概类似中国泡茶中的鱼目和蟹目水的水沸程度,只是前者从听觉的角度讲述,后者从视觉的角度定位。讲究泡茶水沸的程度,是潮汕人泡工夫茶的一大讲究,但是,鱼蟹目水靠打开壶盖去观看究竟吗?并非如此,靠的不是泡茶人的眼力,靠的是泡茶人的听觉。听水,也是一个泡茶人的能耐。
苏轼无疑是懂茶的人,一句“从来佳茗似美人”足见其品茗的境界,更何况还有“活水还须活火烹”的煮茶经验谈。所以,他能着眼于茶的本身去倾听茶的声音。在《汲江煎茶》一诗中就谈到“雪乳已翻煎处脚,松风忽作泻时声”,这是沸水注入茶碗时碰撞翻滚的声音,苏轼却能从注水中听出松风之声,茶中的趣味因此连接了松风之趣,两种来自自然的声音交融在一起。
听茶的趣味,还在于不同品种的茶入壶的声音,铁观音茶形紧实成团,有玉石之感,入壶犹如大珠小珠落玉盘,叮叮当当,清脆声震壶壁;龙井薄条轻巧,倒是轻倏一声就入壶;白毫银针多毫毛,轻软,落壶噗噗两声也就消停;单丛茶长条脆枝,脆脆的几声,随加茶越多,声也就越沉;岩茶较单丛茶粗条一些,入壶略为低沉;白牡丹蓬松,倒像掉进棉花里,一点声响也没有,闷闷地睡着……
深夜的耳朵最适合听茶。
选取一款碧螺春,茶形小巧,半曲,置入盖碗中,窸窸窣窣及触碗底。红炉上水正沸,稍停片刻,提壶高冲,咚咚之声,是清流激石的声响,也是翻滚、疼痛的反弹。放下壶,俯身贴近茶碗,只听见隐隐约约的噗噗呲呲声从茶碗中传来,每一次噗呲的小声响,是惊醒的颤抖,一颤一声,都伴着茶叶的舒展而动。渐渐地,像极刚刚苏醒的慵懒女子在伸懒腰;也有的茶叶在舒活筋骨中从同伴的身上翻滚下来,轻巧地翻了一下身子,制造一次略大的声响;也有的舒展手臂,啪的一声,攀交情似地搭上同伴的肩。然后是放开束缚,义无反顾地挣脱被处理过的束缚,舒展、舒展,像舞者的脚步,踩得碗底砰砰地响,终于绽开成最初的样子——一片片脉络清晰的叶子,安静下来了。
这是一场生命的宣言,当静止下来,茶色泛开。一壶水,让等在时光里的茶,拥有了第二次生命的脉动,若没有安静地听茶,是听不出一番恣意的。
听茶,又何止是茶,何止是生命。若有一心,沧海万物,浮沉、生死、变幻,明灭……皆是耳中音、心中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