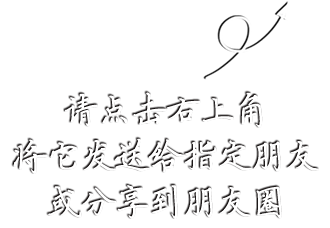□陈爱兰
我家附近有两个卖凉粉的摊点,相隔一步之遥。
路南是位大妈,皮肤白,干练,卖凉粉和咸鸭蛋。路北是个干瘦老头,机灵,除了凉粉和咸鸭蛋,兼有油炸的蚕豆、花生米,以弥补自己的“劣势”,两边和气生财。
一到夏天,两把大伞一撑,两个罩篮一支,罩篮里放着一大团凉粉,稳当地坐着。旁边三四个装满凉粉的小碗,殷勤地站着。各种佐料盒子,随时待命。
一有人问津,卖凉粉的迅速浇上麻酱油,麻利地撮上一点香菜、榨菜、什锦菜,问一句,辣的还是不辣?转眼间一碗色泽缤纷的刨凉粉已递到你面前。
性子急的,站着三扒两咽风卷荷叶。不急的坐在小方凳上,斯斯文文地吃,最后把粘在碗边的粉条,一根一根搛下来,一起夹进嘴里,满意而去。
下班高峰期也是摊点最忙的时候,跟着城市欢快的节奏,两边都围着一群人,总有相熟的,隔空聊上几句。皮肤白的大妈因为忙,白里透红。干瘦的老头因为忙,精神矍铄。更多的人打包,与家人共享。我也常常凑过去,喊一声:“一碗微辣的带走!”
喜欢吃刨凉粉很久了。
三十多年前在县城上班,每天车间、食堂、宿舍三点一线。盛夏的傍晚,回到拥挤的宿舍,闷热难当,离开饭还有一段时间,百无聊赖时,一声悠扬的“卖凉粉啊”从窗外飘来,姑娘们打了鸡血一样,兴奋地拿着搪瓷小盆子,循声而去。
厂门口,一辆三轮车上放着一个大脸盆,揭开脸盆上的毛巾,晃悠悠的凉粉,暗青色,透着盈润的光,像深冬明月。卖凉粉的用一种特制的锼子一圈一圈在凉粉上盘旋,粉条就从锼子的圆孔中冒出来一层层码在碗里,变得莹白可人。加入调料,姑娘们全身心地投入,大快朵颐。
倘若有一天卖凉粉的因事不能来,一个个霜打的、蔫倒在床。等吆喝声再次响起,就像嘹亮的冲锋号,姑娘们蹦起来瞬间没了影。就这样,寂寞难耐的长夏,因为凉粉,变得清凉美好。
刨凉粉好吃不贵,亦上得了台面。如今在豪华的酒店,一桌酒席的冷碟里,常看到一盘刨凉粉,清丽优雅,在其间不卑不亢,极具个性。
刨凉粉搭盐水鹅是夏日一绝。父亲说一素一荤,爽滑香嫩,最能满足口腹之欲。小时候有一回,立下军令状、完成销售任务的父亲,长途跋涉而归,带着一身的风尘,去理发店剪好头,便到凉粉摊买了一大碗刨凉粉,再拐到卤菜店切了半个盐水鹅,犒劳全家。
晚上,小长桌搬到天井里,一家人围桌而坐,父亲把酒言欢,分享旅途的奇闻趣事。
因为热,汗从脖子上往下淌,父亲用毛巾擦一擦,搛一筷子凉粉,咪一口酒,有声有色接着说。我们四个小孩一边听,一边一口凉粉一口鹅肉。那时生活清苦,盐水鹅进家门只是昙花一现,所以那美妙的滋味就像爱情突然出现在青春里,美得让人难忘。不知不觉盐水鹅吃完了,父亲一块也没舍得吃,滋味全给了我们。那一晚,星光灿烂,蝉鸣婉转,我们度过了父亲演绎的一次曼妙时光,记忆犹新。
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称北宋时汴梁已有“细索凉粉”。凉粉的历史不短,一直到今天还活跃在我们的日常里,想来食物的美好,不在于它的金贵,而是自身散发的魔力,人也一样。
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炎夏已至,来一碗刨凉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