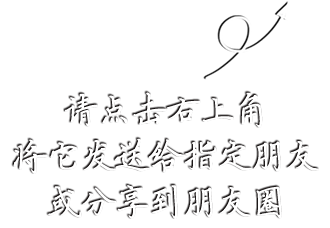□谭银兴
肆
东坡与和陶诗——借渊明的壳,过惠州的生活
《记游松风亭》挂钩之鱼忽而解脱后,苏东坡的诗文里游山玩水、交朋会友、种花酿酒等惠州“苏式”(舒适)生活场景多了起来。
到了绍圣元年十二月,苏东坡开始走出惠州城,他与儿子苏过同游白水山佛迹岩、泡汤泉。白水山就是现在的惠州汤泉,距离嘉祐寺约20公里路程,在那个年代,以花甲之年老人的脚力,往返要一天时间,不可谓不远。苏东坡这趟短游非常开心,连作《白水山佛迹岩》《咏汤泉》,与儿子唱和。其中,在《白水山佛迹岩》写到:
此山吾欲老,慎勿厌求取。
溪流变春酒,与我相宾主。
我就想在这座山里终老,希望不要厌烦我的索取。这里的溪水像岭南万户春酒一样使我陶醉,如同主人一样款待着我这个远道而来的客人。作者流露出浓浓的归老之情。
再后来,他有雅情到江边垂钓:
意钓忘鱼,乐此竿线。
悠哉悠哉,玩物之变。
——《江郊》
这哪是钓鱼?钓的是闲心。
太守詹范带着酒到嘉祐寺探望苏东坡。苏东坡很高兴,两个人来到东江边,从乡间野市备点小菜,简单清扫一下钓鱼矶石当作餐台,对着江风明月畅饮起来。
传呼草市来携客,洒扫渔矶共置樽。
同时一边饮酒一边商议了将江中暴露的无主骨骸集中收集起来安葬。
有得道的世外方人传授他桂酒酿造秘方,他觉得这酒很好,不像人间所有,是“天禄”,认为不能独享,便在桥下置石刻广而告之,并写下《桂酒颂》。
但凡有一点机会,苏东坡心里装的都是忧国忧民的事。
第二年开始,来看望苏东坡的朋友和南北往来的信件渐渐多起来了。惠州太守詹范自不待说,连周边地区的循州太守周彦质也接济他米粮,梅州谭太守还专程派人赠送他酒水。更有僧人、道士、秀才等高雅之士往来,日子好不惬意。不久又有好消息传来,表兄兼姐夫程正辅任广南东路提刑官巡按广州,专程托人带口信到惠州向苏东坡致意问候。苏东坡也马上回信,希望能够冰释前嫌。
到了三月份,友人卓契顺以“惠州不在天上,行即到耳”的侠义,从宜兴徒步两千多里路程到惠州带来大儿子苏迈的家书,更让东坡动容。
在这轻松惬意的环境中,苏东坡的唱和之作多起来了。也许是前世的因缘,更愿相信是惠州给予诗人灵感,诗人写起了和陶诗,并且一发不可收拾,竟写了50多首(后在海南儋州接着写,和遍109首),在寓惠诗作中占了很大篇幅。正如他弟子黄庭坚所言,苏东坡是“饱食惠州饭,细和渊明诗。”
“和陶诗”,顾名思义,就是以效仿陶渊明诗歌的韵为形式而创作的诗。世上原没有和陶诗,因苏东坡写多了就变成一种和陶诗。
苏东坡写和陶诗的一大原因就是仰慕陶渊明,因仰慕而和韵。这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一场隔着600多年时间(东晋与北宋)、1000多公里距离(彭泽与惠州)的唱和,两个伟大心灵的对话与交流,其共鸣让后来无数诗人跟风,争相模仿,竟然成为一种文学现象。
苏东坡说,我可能前世就是陶渊明。(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我即渊明,渊明即我也。)
苏东坡说,我人生的悲剧就是因为学不到陶渊明对仕途的舍弃。(我不如陶生,世事缠绵之。)
到最后,苏东坡说,我写了109首和陶诗,水平跟陶渊明比起来也不差了。(吾前后和诗一百有九,至其得意,自谓不甚愧渊明。)
苏东坡最早和陶诗的渊源可以追溯到黄州时期,同样是谪居的苦旅,他改编了渊明的名篇《归去来兮辞》,写成《哨遍·为米折腰》:
为米折腰,因酒弃家,口体交相累。归去来,谁不遣君归。觉从前皆非今是。露未晞。征夫指予归路,门前笑语喧童稚。嗟旧菊都荒,新松暗老,吾年今已如此。但小窗容膝闭柴扉。策杖看孤云暮鸿飞。云出无心,鸟倦知还,本非有意。
真正创作和陶诗始于元祐七年(1092)七月,即时贬谪到惠州的前二年。那时的他虽仕途上如日中天,但因政敌无端攻讦,已萌生退意,羡慕陶渊明能够摆脱俗事羁绊,写下了《和陶饮酒二十首》。
创作和陶诗的高峰期是在惠州。自绍圣二年三月四日,苏东坡与詹范太守等人一起再游白水山,回程时路过水北荔枝浦(今惠州江北),遇到园主85岁“平生不渡江”的水北老人,彼时荔枝才像芡实那么大小,老人热情邀请苏东坡待荔枝成熟时还要回来,管够食饱还要打包带走。回到嘉祐寺,苏东坡很有感慨,在回复一生挚友陈慥的信中说到“到惠将半年,风土食物不恶,吏民相待甚厚。”有感于此,苏东坡重新写起了和陶诗《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并在引言中立志要和遍陶诗。
其一
环州多白水,际海皆苍山。
以彼无尽景,寓我有限年。
东家著孔丘,西家著颜渊。
市为不二价,农为不争田。
周公与管蔡,恨不茅三间。
我饱一饭足,薇蕨补食前。
门生馈薪米,救我厨无烟。
斗酒与只鸡,酣歌饯华颠。
禽鱼岂知道,我适物自闲。
悠悠未必尔,聊乐我所然。
其二
穷猿既投林,疲马初解鞅。
心空饱新得,境熟梦余想。
江鸥渐驯集,蜑叟已还往。
南池绿钱生,北岭紫笋长。
提壶岂解饮,好语时见广。
春江有佳句,我醉堕渺莽。
其三
新浴觉身轻,新沐感发稀。
风乎悬瀑下,却行咏而归。
仰观江摇山,俯见月在衣。
步从父老语,有约吾敢违。
其四
老人八十余,不识城市娱。
造物偶遗漏,同侪尽丘墟。
平生不渡江,水北有幽居。
手插荔支子,合抱三百株。
莫言陈家紫,甘冷恐不如。
君来坐树下,饱食携其余。
归舍遗儿子,怀抱不可虚。
有酒持饮我,不问钱有无。
其五
坐倚朱藤杖,行歌《紫芝曲》。
不逢商山翁,见此野老足。
愿同荔支社,长作鸡黍局。
教我同光尘,月固不胜烛。
霜飙散氛祲,廓然似朝旭。
其六
昔我在广陵,怅望柴桑陌。
长吟饮酒诗,颇获一笑适。
当时已放浪,朝坐夕不夕。
矧今长闲人,一劫展过隙。
江山互隐见,出没为我役。
斜川追渊明,东皋友王绩。
诗成竟何为,六博本无益。
第一首开篇就以“环州多白水,际海皆苍山。以彼无尽景,寓我有限年”描写了惠州的好山好水,表达了终老惠州的愿望。紧接着以“市为不二价,农为不争田”举例子,写下惠州人爱读书、遇事不争的淳朴和善民风。又以“门生馈薪米,救我厨无烟……悠悠未必尔,聊乐我所然”写了自己虽生活上需要门生接济柴米,但是日子怡然自得、优哉游哉。
接下来几首也分别描写了游白水山、泡温泉、趣遇水北老人的情景。尤其是最后一首,点明自己在扬州时候就很向往陶渊明的生活,现在这里(惠州)就如斜川和东皋,有着陶渊明世外桃源般的生活和一群像王绩一样不流于世俗的酒友。整组诗,明快、怡然的田园之风扑面而来。
至此,和陶诗成为苏东坡寄托思绪的重要载体。
过节写和陶诗。绍圣二年重阳节,苏东坡来惠已经近一年,生活愈加窘迫,又逢佳节思念散落天各一方的子侄家人,于是作了《和陶贫士(七首)》。既“典衣作重阳,徂岁惨将寒”,为了过重阳把厚衣都典当了,哪还顾得上即将到来的寒冬?朝不保夕的困境;还有“我家六儿子(含三个侄子),流落三四州”的人伦别离和思念,读之令人心酸。
读书写和陶诗。东坡读葛洪《抱朴子》深有心得,想到陶渊明读《山海经》的故事,隔着时空,苏东坡与陶渊明、葛洪“对话”起来,写下《和陶读山海经》,“携手葛与陶,归哉复归哉。”那一刻,在苏东坡的精神世界里,三个人是携手同游,一起归隐桃花源。如今,东坡祠里的三贤祠正是三者关系写照的具象。
迁居写和陶诗。绍圣三年(1096)三月,苏东坡从合江楼复迁水东嘉祐寺,第二次居住嘉祐寺的心情与第一次已大不相同,更多是自愿、开心的成分。在合江楼居住的一年时间里,东坡“多病鲜欢,颇怀水东之乐”。于是在白鹤峰买地数亩作新居,同时迁回嘉祐寺居住。为此,苏东坡写下《和陶移居》。作者以“晨与鸦鹊朝,暮与牛羊夕”之句,形容嘉祐寺居住环境的“幽深窈窕之趣”(《题嘉祐寺壁》),与初到惠州刚入住嘉祐寺时的“蛮风蜑雨愁黄昏”心境已迥然不同。
会友写和陶诗。绍圣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临近过年。彼时,白鹤新居正在营建中,东坡财资竭尽,生活困顿,但是依然热情招待远方而来的两位朋友。这天酒喝完了,想取米酿酒,发现米也吃完了。想到陶渊明《岁暮和张常侍》一诗也以无酒而感叹,便作《和陶岁暮作和张常侍》将此事记载下来。“米尽初不知,但怪饥鼠迁”家里穷到连老鼠都嫌弃,诗人的笔触诙谐,让人好笑之余未免心酸。“二子真我客,不醉亦陶然”充分体现出作者交友上的真性情。
伍
东坡寓惠文化:属于双向奔赴的美丽
经过嘉祐寺松风亭边的“悟道”,苏东坡儒释道思想更加交融,进退切换更加自如,进入了更高层次的“自由王国”境界。
在惠州居住的最困难时候,表兄兼姐夫程正辅来广东做大官,他以天子“近臣得罪,省躬念咎”为由,稳坐嘉祐寺,等程正辅上门探访。等见面尽释前嫌后,送程正辅离开,苏东坡一送就送到博罗罗浮山下,并且连夜商议募建东新桥事宜。得到程正辅支持,有了干事机会,苏东坡马上切换另一种状态,以极大饱满的儒家济世精神积极奔走,出谋划策,带头募捐,推动“两桥一堤”建成。
在程正辅调动离开广东时候,又得知元祐党人永不赦还消息,苏东坡买下白鹤峰建新居,“规作终老计”,对来回搬迁的生活,苏东坡笑侃是“东西两无择,缘尽我辄逝”。对此变动,他已抱着“吾生本无待,俯仰了此世”随缘心态,认为万物都是“念念自成劫,尘尘各有际”,充盈着“齐万物、泯是非、破生死”的道家思想。
后来,家中遭遇瘟疫,跟随苏东坡23年、一路辗转南北,无论升陟贬黜、始终陪伴身边的爱妾朝云病逝。面临如此大的打击,尽管苏东坡心中万分悲怆,但没有发凡俗情侣“生生世世为夫妻”的誓愿,而是祈愿她能够超脱生死轮回,进入仙佛境界,自己也将在余生勤修佛道,期待与她在佛国净土相会,写下了“驻景恨无千岁药,赠行惟有小乘禅。伤心一念偿前债,弹指三生断后缘”(《悼朝云》)之句。在惠州,舞衫歌扇早已成为过去的梦影,朝云和他一道参禅学道,已超越红粉佳人,是同甘共苦的知己、是修心养性的挚友。在苏东坡心中,朝云就是天女维摩。
在惠州嘉祐寺里松风亭边,苏东坡以咏梅诗和和陶诗为主要载体,实现人生再次突围,完成思想再次升华,再无哀怨,书写了岭海谪居人生最后一段苦旅的精彩,也为惠州留下了无比珍贵的东坡寓惠文化。
东坡寓惠文化,是诗人的人生历程与惠州这块土地产生的化学效应和思想结晶。惠州人文地理环境与苏东坡寻找世外桃源的理想追求相契合。这里既远离中原,但又不是蛮荒之地,而是山水秀邃,风土人情甚厚,有山、有水、有松、有梅,有僧、道、科考失败者、游侠、隐士、酒者为伍。品格、命运、地理三者的因缘际会,成就了东坡寓惠文化。
东坡寓惠文化,不是东坡文化以时间为尺度的简单裁剪,也不是某些学者眼中已过创作高峰的作品,更不是一些人口中的贬官写照,而是有着鲜明的文学特征和地域特点,在东坡文化中占有重要一席。诚然,在惠期间苏东坡的作品没有了“大江东去”的雄心勃发,也少了很多广为传颂之作,但是“流量”不代表“质量”,寓惠时期他诗词境界上更加高洁、思想上更加纯臻,言语上更加质朴无华。也正是这种特征,导致趣味性不强,普通读者难于进入,是阳春白雪、曲高和寡而已。可以说,东坡寓惠文化是苏东坡赠予惠州这座城市的宝贵人文遗产。同时也可以毫不吝啬地说,惠州也给予诗人人生末段旅程最后的足够的温暖。
东坡与惠州虽是意外轨迹的交集,却属于双向奔赴的美丽。
每个时代关于苏东坡都有不同的回答。
每个人关于苏东坡都有不同的解读。
尾记
东坡走过的路道
已经堙灭
东坡的脚步声
还在惠州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