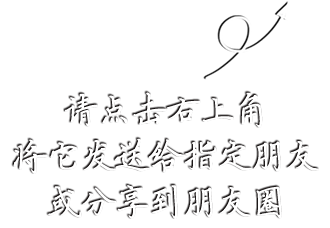□李桂根
“垂緌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虞世南的诗句,总让我想起童年夏日与蝉有关的种种乐趣。那时,和弟弟在树林里搜寻、捕捉知了猴(蝉的幼虫),是我们乐此不疲的开心事。
盛夏的白日,浓密的树荫下,我们低着头,目光如炬,细细搜寻着地上的小洞。知了猴在暗无天日的地下,吮吸树根汁液,蛰伏数年之久。待成熟时,它们会在白日里向上掘洞,只待夜色降临,便奋力爬出,攀上树干,完成生命中最壮丽的一次蜕变——羽化成蝉。我们深谙其道,专找那些绿豆般大小、洞口薄脆的孔穴。手指轻轻一按,泥土应声塌陷,露出浑圆的洞口。指尖探入,触到那硬实微凉的身体,轻轻搅动,知了猴便紧抱着我们的手指,被顺势拉出幽暗的地穴。
捉回的知了猴,悉数被我们安置在蚊帐内。它们是攀爬的高手,很快便吸附在帐壁四周,牢牢抓稳,静待那神圣一刻的到来。蜕变的过程奇妙而缓慢:先是背部悄然裂开一道缝隙,接着在一次次微不可察的颤动中,柔嫩的肢体——臂、头、上半身、羽翼——逐一挣脱束缚,最后全身奋力一扭,尾部彻底脱离旧壳。初生的蝉通体淡绿,湿漉的翅膀粘连着,随后体液管迅速充血,薄翼渐次舒展、挺立,变得轻而坚韧,身体的颜色也由绿转深,向着墨色沉淀。
我们收集知了猴,主要是为了攒下它们蜕下的空壳——蝉蜕。那是味药材,药店会收购。也曾听闻知了猴可食,只是我们这里没有人尝试过。一次,好奇心驱使,我和弟弟在灶膛里烤制。当特别的清香随热气升腾,猛烈冲击着味蕾时,我们终究在食欲与迟疑间徘徊,只得以鼻息贪婪捕捉那诱人香气,未敢下口,最终成了犒劳鸡鸭的佳肴。
“密槐高柳覆华堂,满地熏风白昼长。却怪蝉声惊客思,不容蝶梦到吾乡。”炎夏正午,热浪翻涌,嘹亮的蝉鸣与灼人的暑气交织,搅得人无法安眠。被搅了午梦的我们,索性拿起捕蝉的工具——面筋。和好的面团在水中反复揉洗,洗出黏性十足的面筋,再缠缚于长竹竿顶端。循着密集的蝉鸣,潜入树林,发现目标,屏息凝神,竹竿悄悄伸近,趁其不备,迅疾一靠,那鸣叫的精灵便被牢牢粘住,挣扎着落入我们的掌心。装蝉的布袋里,公蝉鼓噪高鸣,母蝉则扑棱着翅膀,好不热闹。
提着战利品归来,鸡鸭早已躁动。几只鸡伸长脖颈,乍开翅膀,踏着细碎轻快的步伐冲刺而来;鸭子也不甘示弱,摇摆着笨拙的身体,“呱呱”叫嚷,仿佛在催促“快给我一个!”。鸡虽跑得踊跃,吃相却远不如鸭爽利。捏出一只蝉,掐去翅膀,先抛给鸡。鸡用喙反复啄弄,蝉发出凄厉的鸣叫,从清亮到嘶哑,直至呜咽,鸡往往折腾许久才能肢解一只。鸭子则大不相同:长颈一伸叼住,仰头几个干脆利落的吞咽,蝉便滑入嗉囊。有时,鸡若动作稍慢,吃剩的蝉会被意犹未尽、眼疾手快的鸭子抢去。一次,鸭子抢了小母鸡的食,惹得护妻心切的大公鸡怒不可遏。它昂首挺胸,踱着稳健的步子逼近,红冠如火,羽毛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威风凛凛。鸭子毫不示弱,扑腾翅膀,摇晃身躯,摆开架势。目光如电,对峙一瞬,公鸡猛地前扑,尖喙直啄鸭头!鸭子反应极快,侧身翻滚躲过,随即张开扁嘴猛烈反击。公鸡腾跃而起,翅膀扑打……一时间鸡毛鸭毛漫天飞舞,上演了一出活灵活现的“鸡争鸭斗”图。
转眼数十载光阴逝去。童年林间的蝉鸣,蚊帐里静待羽化的知了猴,布袋中喧闹的俘虏,还有那场为蝉而起的鸡鸭大战……一幕幕清晰如昨,裹挟着夏日的热风与泥土的气息,在记忆深处悠扬回响,久久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