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海军 想起罗浮山,心中总会涌起一股莫名的情愫,想再次踏上那片土地,去细细品味那些曾经的过往。从大学毕业到转业地方足足十五年,而后在地方工作已然八个年头,二十多年的岁月啊,我人生中最璀璨的黄金岁月始终在那儿度过。那山间的一草一木,那山脚的一户一人,虽已深深刻画于心,但那份独有的情感,依然如血脉般流淌在身体的每一个角落,难以割舍。 那一年,我军校毕业,被分配到了罗浮山部队。从北方学校出发,火车转汽车,汽车又转小巴,那辆除了喇叭不响外哪里都在响的小巴车,风驰电掣,一路颠簸,末了,穿过一条蜿蜒曲折的山路后,司机扶着方向盘,大声喊“部队到了”。我迅速抬眼朝窗外看去,远处青山连绵,峰峦叠嶂,云雾缭绕间难见山巅。四周被茂密的林木紧紧包裹,即便是那曲折的山路,两旁亦是绿荫如盖。然而,就在这葱郁之中,一座雄伟的军队大门楼巍然屹立,门楼之巅,八一军徽在落日余晖中熠熠生辉,庄严而神圣。 门口的哨兵见我下车,迅速从值班室走出来询问。得知我是新排长来报到,随即电话通知集训队。不多时,一个士官匆忙赶来,热情地自我介绍自己姓黄,说着,转身提起我的行李,一行两人步入军营。穿过一条笔直宽广的大道,黄士官向我提议抄近道,引领我转向了一条环山小径。 小径幽深曲折,仅能容两人并肩而行,但沿途风光旖旎,美不胜收。我初次见识了诸如桫椤、棕榈、小叶榄树等树种,林中,各种不知名的鸟儿在欢快鸣叫,一只只松鼠在树枝间肆意跳跃,夕阳透过树叶洒下,留下一地斑驳的光,那份生机与活力,瞬间驱散了我从繁华都市坠入寂静乡野的淡淡忧伤。 穿过茂密的丛林后,眼前的小径豁然开朗,一间低矮的土坯房映入眼帘。我心中一阵诧异,南方的营区居然也有农户。正当疑惑之际,一声清脆的“敬礼”打破了宁静。我循声望去,只见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站在屋前,高高举起稚嫩的小手,有模有样地敬着军礼。我细细打量这男孩,头戴略显宽大的迷彩帽,帽檐遮住了大半张脸,只露出一双乌黑晶亮的眼睛。他光着膀子,仅穿着一条部队配发的淡蓝色细纹格子内裤,因尺寸过大,被提到了胸前。脚上穿着一双大号棕色拖鞋,露出黑黢黢的小脚丫。 正当我惊讶之时,黄士官大喊一声“敬礼”,庄重地向小男孩回礼。没一会儿,黄士官又喊了一声“礼毕”,两人面对面整齐划一地放下了手。 “阿望,你在啊?我还以为你又去捉鱼了。”黄士官走近小男孩,笑呵呵问道。 “黄叔叔,我捉鱼回来了,今天捉了好大一条。”阿望兴奋地说。 黄士官乐了,向阿望竖起大拇指,说:“呀,阿望厉害了,阿望真乖,来,把这个饼干拿着。”说着从迷彩服裤兜里掏出几大包压缩饼干递给他。阿望双手捧着堆成小山的饼干,连声说着谢谢,转身跑进屋里。不一会儿,一个满头白发、佝偻着身子的老奶奶拄着拐杖,被阿望牵着走了出来。老奶奶连声说着感谢。我虽听不懂老阿婆的客家话,但仍然能够明显感受到老奶奶的感激之情。黄士官赔着笑,连忙安抚道:“阿婆,不客气,我们改日再来啊。”说着,转身带着一脸茫然的我匆匆离开。 我们俩并排前行,空气迅速安静下来,能够清晰地听到彼此的脚步声,以及远处时不时传来的鸟叫虫鸣。良久,黄士官不经意间一扭头,看着满面疑惑的我,神秘一笑道:“排长,你是不是很好奇刚才的事啊?” 初来乍到的我未置可否,只是朝黄士官回报了一个笑容。 黄士官边走边讲起那段尘封已久的故事: 抗日战争时期,活跃在罗浮山下的东江纵队为积极宣传党的主张,请博罗进步人士陈洁募资采购了一台印刷机,创办了《前进报》。1944年日寇扫荡时,机器转移至罗浮山交由前进报社使用。后来部队奉命北撤,为避免敌人搜查,机器临时被拆散成若干小零件,一部分埋入深山,一部分交由罗浮山下的两家农户代为保存,而阿望家便是其中一户。那时阿望的太爷还像如今的小阿望一样大年纪,对游击队员的话一知半解,从他们的话语中仅仅记住了“播种机”三个字。不久,当敌人搜查至此,询问时,他不明所以地讲出了“播种机”,竟让敌人全然未料到孩子口中的“播种机”就是印刷机,从而使其得以完整保存下来。随着日本人投降,众人将分散的零件重新组装,印刷机重见天日。后来,阿望的太爷参加了抗美援朝,退伍归来后,在罗浮山下建房,与军营比邻而居。阿望的三个爷爷又都当了兵,一起去了西南,却只回来了一个。如今,阿望的父母都去了外地打工,他与寡居的奶奶相依为命。官兵们因而时常接济阿望。久而久之,大家便与阿望成了不是战友的“特殊战友”。 听黄士官讲完,我心头萦绕起一种难以言喻的情绪,而阿望那瘦小的身影,却如同幻影般在脑海中挥之不去。自此以后,只要有时间,我也会同大家一样,拎着大包小包去阿望家坐坐,逗逗阿望开心,陪陪老阿婆说说那些懂与不懂的客家话。在众人的关爱下,小阿望也渐渐长大。 后来,我从罗浮山转业到了地方工作。离开军营之际,我特意前往阿望家。这一次,阿望父母在家,而他却正好在外地上大学。通过阿望父亲的微信,我和阿望进行视频通话。他正在学校图书馆看书,身着运动服,皮肤晒得黝黑。熟络的人迅速打开了话匣子,我们的话题从罗浮山畅聊到了脱贫攻坚。阿望说:“现在我们村在搞脱贫攻坚,我在学校参加不了,但我相信,建设我们村,什么时候参与都不晚。等我毕业了,也回罗浮山,回去建设我美丽的家乡,像‘播种机’一样,播种快乐,播种美好,播种幸福,播种希望。”这一瞬,虽隔着屏幕,我依然能够清晰地看见阿望那双亮晶晶的眼睛里闪烁着坚定的光芒。而他那自信的言语,于我而言,更像是一台真实可感的“播种机”,正在为美好未来播种下希望的“种子”。 从阿望家的红砖房出来,已是夜晚。我信步走出军营,漫步在那条乡间小路上。罗浮山的夜空繁星点点,一轮明月高悬,如同油漆匠般将整个大地涂抹上了一层明亮的月光,身边树影婆娑,小路旁早已排列起了一栋栋整齐的小楼,灯火或明或暗;远处传来阵阵蛙鸣声,声音或高或低。在小路边的不远处,正在修着一条更宽阔的大路,路上灯火通明,机器轰鸣,人来人往。那一刻,蛙鸣声与机器轰鸣声交相辉映,犹如一曲动人的交响曲,莫名地和谐,又恰似一股清泉,汩汩流淌在每个人的心上;而那月光与灯光交织在一起,将整个热火朝天的工地照得通明透亮,为每一个忙碌的身影和机器披上了一层瑰丽的光彩,熠熠生辉。 不知不觉中一晃又是数年,时间悄然来到了2024年。这一天,我随单位工作组再次踏上了罗浮山。下罗浮山乡村工作早已不知是多少次了,然而,这一次的一路上,同事们都开始热情洋溢地讨论起了环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建设的点点滴滴。我默默聆听,思绪却始终徘徊在往昔的回忆中,只是,我的脑海里早已没有了阿望瘦小的身影,取而代之的是他在视频中露出的淡淡笑容和那台神奇的“播种机”。 工作组一路走访,接连转了三个村,最后来到了一个村委会。在人群中,我一眼便发现了阿望。他穿着一件淡蓝色的T恤,手里抱着一摞文稿,远远看见我,连忙上前来打招呼。谈话间,我得知他大学毕业后便回到了罗浮山,应聘做了一名大学生村官。现在,他正协助村支书,忙着借“环两山”示范区建设的东风,全力推动朱顶红种植产业。 工作组在村支书和阿望的带领下,来到他们口中的朱顶红种植基地。望着那一大片盛开的色彩斑斓、犹如牡丹花般硕大的朱顶红鲜花,书记自豪地侃侃而谈,阿望也在我身边小声讲解。尤其是从种球引种价格到鲜花售卖价格,再到中间差价及给农户带来的收益,那些纷繁复杂的数字账目,他竟能脱口而出。不经意间,我看见他那双大眼睛依旧亮晶晶的,闪着光,虽然眼袋已深,但仍炯炯有神、神采奕奕。末了,我调侃他这台“播种机”在家乡的土地上播下了希望的种子,有没有为自己的人生也播下“种子”。一旁的书记接过话茬,笑呵呵地说:“他的种早就种下了,两个小阿望都满地跑了,哈哈哈……”书记的一席话引得众人欢笑连连,而阿望则一脸羞涩地挠头,红着脸。 看完鲜花基地,我随工作组登上回城的汽车。书记和阿望在路边挥手告别。当我回头再次望向他们时,突然发现又是一个夕阳西下的时候,那琥珀色的晚霞披在他们身上,显得格外灿烂。两个瘦高的身躯如同两台播种机,在这片火热的土地上辛勤地播种着未来。而身后的罗浮山,依旧巍峨挺拔,翠绿如初,白云悠然。我想,它或许正静静观望着山脚下这群如阿望一般的年轻人,在时代的洪流中挥汗如雨、砥砺前行,热火朝天地建设着自己美丽的家园。 从罗浮山归来,我辗转难眠,因为我还想再次踏上那片山美水美人更美的土地,再走一走那通往远方的康庄大道,尤其是想再去看一看那一台存放在东江纵队纪念馆里的“播种机”……
-
即时新闻

播种机
来源:羊城区域
2025年05月30日
版次:ZHA16
栏目:
作者:席海军
分享到微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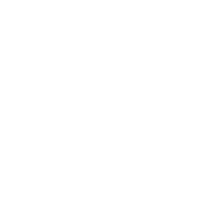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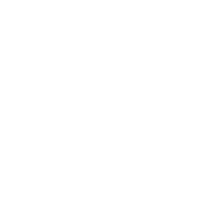
使用"扫一扫"即可将网页分享至朋友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