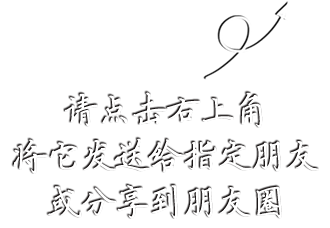□武桂琴
朵朵是我从2021年开始收养的一只三花猫。一旦我离开家两三天,朵朵就会变得不爱吃饭、不爱运动,过着凑凑合合讨好一下喂养它的人然后懒洋洋躺着的日子。若我回到家里,她第一时间启动欢呼雀跃模式,进行满屋狂奔式宣泄,紧接着嘴里吵吵着一堆话,叽里咕噜一堆谴责过后,才算解了它的心头大闷。然后,便不再是懒洋洋凑合着过日子的猫,而是那个追求猫生质量的猫,到点主动申请加餐,加什么餐也有具体要求,达不到目的它就用嘴衔着你,引导你到它的餐饮区,然后按照抬头不算低头算的表达方式,一遍又一遍唤醒你,直到实现它的愿望为止;还会主动要求一起捉迷藏,主动申请吃草,申请的方式是对着露台引导式叫唤,喋喋不休,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每当它喋喋不休的时候,也是我陷入奇思的时候。按说一只猫并不具备“正直勇敢有阅读量”的天赋条件,所有的认知都来源于它自身的感觉和判断,但是它解决了如何与人类正常相处的大部分问题,而且察言观色辨别力又那么上乘,令人怀疑人类在一生中用于不断学习的时间是不是太长了?如果不需要创造灿烂的人类文明,仅仅只是解决温饱和安逸,也许人类的自发能力不见得比一只猫一只狗更厉害吧。
回顾一下从小到大近距离接触过的动物,貌似每种动物都有一些刻在DNA里的天赋能力。
小的时候,家里曾经养过鸡。一般是一两只公鸡和一大群母鸡生活在一起,它们散养在院子里,吵吵闹闹、争奇斗艳,很少有和谐的时候。鸡虽是群居动物,但鸡与鸡之间似乎没有友谊而只有相处,日常也并不见它们在任何情况下发生相互依偎的情况,它们只是日出而鸣,日落而歇,喜欢各自在自己认定的地方下蛋,每次下完蛋从不静悄悄,一定是引吭高歌的。
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只花母鸡活了十二年,最后那一年它已经不下蛋了,每天努力爬到一个能晒到太阳的架子上,一直晒啊晒。就是在那个夏天,它选择了躺在阳光下这块熟悉的地方静静地等待天授。最后,它在午后的阳光里永远地睡过去了。母亲说它是一只立过大功的母鸡,给它找了一处地方掩埋了。它大约是鸡群中难得的一只寿终正寝的鸡。
养过猪。猪圈实在是太脏,没有任何卫生的保障,只在猪圈角落的猪窝里放一些干草保持干燥,吃的也不过是剩饭剩菜或者米糠之类的,夏天的时候尚可以吃到猪草。无论如何,家养猪度过的都是潦草而短暂的一生,到了年根儿,它们便只有接受它们同类相同的宿命。
养过兔子。不记得兔子后来的命运了,大概是成年后就被卖掉。记得采了兔草带回去,看他们吃得很欢快的样子,竖起的长长耳朵灵活又警觉。比起猪,兔子很喜欢讲卫生,喜欢自己打理自己的地盘儿。
养过驴。是一头健硕的母驴,它后来还产过一头小驴,像它一样有着优美健硕的身材。我对驴的所有记忆都停留在“勤劳”二字上,它承担着负重前行的任务,物品太过于沉重时它就本能地屈膝,但凡能背得动它便无言地前行。人类对牛马驴这种大型食草动物的驯化是最成功的,除非遭遇极限压迫,否则它们几乎不作任何反抗。
养过鹦鹉。不会说话的那种小鹦鹉,好看是好看的,每天欢快地叽叽喳喳着,可惜有一次出差时间太长,饿死了一只。刚发现时,米盒里其实仍有一丢丢的小米,但是它饿死了,确保了另一只活了下来。然而,活下来的那只后来越来越不爱叫,有一天也在沉默中离开了。
这么数下来,也算养过不少动物。每一种动物都各有天赋,与人类磕磕巴巴地相处,寻求与人类共命运,但是物竞天择,它们毕竟过于弱势,无法自主选择自己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