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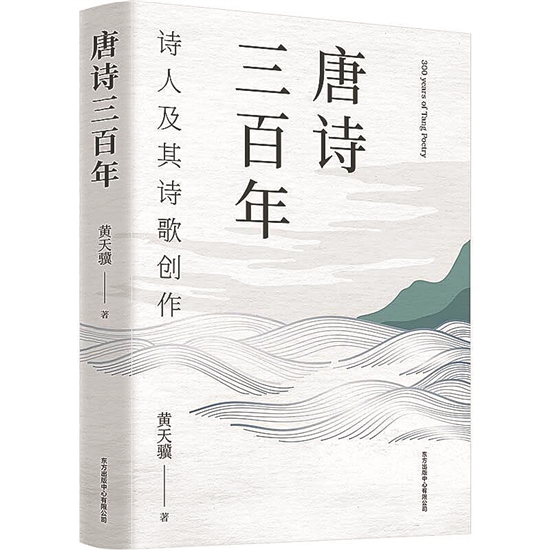
|
|
|
□文/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 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黄天骥新书《唐诗三百年——诗人及其诗歌创作》近日出版,通过解读唐代32位诗人的35首代表性作品,呈现了有唐一代诗歌精华风貌。 该书可谓黄天骥教授从教六十余年来诗歌创作与研究的结晶。黄天骥教授幼承家学,后又从詹安泰、黄海章等前辈学习诗词,在教学研究生涯中,虽然以戏曲为主,但也长期讲授诗词,并出版过《黄天骥诗词曲十讲》《诗词创作发凡》《冷暖室别集》等。 日前,黄天骥老师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 不能脱离时代背景研究古典文学 羊城晚报:《唐诗三百年》的写作缘起是什么?为何是“三百年”而非“三百首”? 黄天骥:这本书其实并非出于一个宏大的写作计划,只是从偶然的单篇文章开始的。2019年初退休后,我住在校外,当时在做一个戏曲的题目,研究了一半因为资料欠缺暂时搁置了,一些学生就说让我写一些关于唐诗的短文章。 1956年,我从中山大学毕业并留校任教,主要方向是古代戏曲,但也一直从事古代文学史的教研工作,所以写唐诗对我来说也算熟悉。 一开始写的时候并没有按照年代给诗人排序,后来成书的时候才发现把作家的年代排下来,可以看出唐诗三百年走过的历程,其实这也跟我研究诗词一向的思想有关:对任何一篇诗词或者一个诗人的评价,都不能脱离所在的时代背景。因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面貌,个人情感的抒发跟时代有着密切的联系。 所以我总要求自己做古典文学研究的时候,不能只看树木不看森林,也不能离开森林去看一棵树木。唯有如此才能准确理解每一篇作品真正的意义和技巧。 羊城晚报:《唐诗三百年》和市面上众多此类出版物有何不同? 黄天骥:现在赏析唐诗,很多人都会把诗歌中的某种精神抽象出来,比如李白诗中表现出来战胜困难的自豪,然后让大家从诗中找到学习的力量,或者单独抽出来某个词进行赏析,我觉得文艺作品不能这样解读,这是非常机械的教条主义式的做法。 如果说我这本书有什么不同,可能就是我不仅要写唐诗如何好,更要说明好在哪里、怎么写出来的。从古代到现在,很多人赏析古诗词往往停留在“如何如何好”,金圣叹评点式,缺乏文学理论层面的分析。我不敢说我自己写得就有多好,但是如果能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对同一首诗的理解,我觉得就够了。 羊城晚报:这么多年游历唐朝诗人及其诗歌精神世界,有何感触? 黄天骥:小时候读唐诗根本读不懂,就是背诵。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都是我祖父叫我背唐诗,但是记忆力很好,《长恨歌》等都能背得烂熟。 在人生不同的阶段读唐诗感受都会不一样。比如唐诗中最常见的《登鹳雀楼》,字面上看谁都明白,所以很多人把这首诗当成风景诗来看,气势宏大,视野开阔,我小的时候就是这样理解的,但是现在完全不这样看,这首诗根本就不是风景诗,而是一首哲理诗,只是借着风景来写。 一个经典的文本,在不同年龄阶段理解是不同的。就像一个外国的汉学家所说,每过20年《西厢记》就应该重新研究一遍,我觉得这个道理是对的。如果一个作品像一张白纸一样明白清晰,那可能是蹩脚的作品;好的作品往往会给人以神秘感,这才有味道,才会耐人寻味。 再也没有第二个李白、杜甫 羊城晚报:在新书中,您不止一次提到了诗人对个人价值的认知,您对唐代诗人对人之价值的认知如何评价? 黄天骥:我觉得中国古代诗词一个很重要的价值,就是不同时代的知识分子都力图要表现出人的价值。比如常见被贬之后写诗发牢骚,其实就是肯定自己的价值,我这么有才能为什么不重用我?为什么这个社会让我无法发挥自己的才能,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这个牢骚其实就是对个人理想价值的一种追求,唐诗里面就有很多这样的作品。 李白、杜甫都有着强烈的个体意识,个性很强,这也是他们能写出如此伟大的诗歌的原因之一。像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鲜明表达了他个人的意志。诗人如果没有这种意识,不注重个人的存在价值,就很难写出好的作品,写的可能是沦为口号式的作品。 羊城晚报:您觉得唐诗取得如此辉煌成就的原因是什么? 黄天骥:两个方面。从社会来看,如果一个社会是开放的,它的文艺作品、文艺思想、对现实的批判和感受往往是放得开、写得深的,而唐代就是这么一个时代。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唐代是最开放的社会,而且神奇的是,唐代越艰难的时候越开放,像安史之乱时期,经济大破坏,人民生活非常痛苦,但是当时的社会能够接受各种不同的文化,开放到连当朝的皇帝都可以批评。从艺术技巧来看,唐代刚好接受了近体诗的写法,既注重语言的韵,也注意平仄的安排,也就是音节的对立统一。这也是诗歌发展到非常成熟的时候才会出现,开放的社会叠加艺术本身的突破,造就了唐诗在中国文学史上不可逾越的地位,再也没有第二个李白、杜甫了。 羊城晚报:对当下的文学创作有何启示? 黄天骥:要从个人视角去看时代,而不是为了写时代而创作。当你从个人视角出发,也不用担心有没有呈现时代,因为一个人的遭遇、情感、感受都是无法脱离时代的,所以写出来的作品自然能表现出时代的精神。到底什么是时代精神,说起来就很广了,不是几句话能概括的,但是能够把那个时代人民普遍的愿望、情感表达出来,就是好的诗歌。 继承传统文化勿忘“优良”二字 羊城晚报:您在研究古代文学时会受到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吗? 黄天骥:会的。中国文学理论的核心是“我注六经,六经注我”,评论家同时是读者,既要把古人的经典说清楚,也可以从主观的方面去阐释经典,为我所用,这是中国传统的文献注释方法。我的老师詹安泰先生曾下定决心“三年不读线装书”,大量地研读政治和文艺理论著作,一心想提高理论水平,加强对中国古代文学发展规律的研究,改变“评点式”的鉴赏方法,这对从旧时代过来的文史研究工作者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当时读的那些文学理论,虽然有的比较教条主义,但是有一点很重要,训练了我们的逻辑思维。 但是也不能盲目使用西方文学理论,比如符号学,某一个形象出来后,经过共同认可变成一种概念性的东西,就是符号,每个民族都有,中国也有。我们不把这作为分析文学的主要手段,因为中国文学理论不会把整篇作品都看成是一个符号的表达,这是中西方文学理论重要区别之一。 羊城晚报:学习、研究古代诗词有什么现实意义? 黄天骥:对我们中国人来说,要进一步认识到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和伟大意义,增强我们的民族自信心,这在当下是非常必要的。尤其是现在,西方文明值得我们学习,但也不能忘了中国的古代文明,我们有自己一套行之有效的社会标准、社会规范,文学上也有一套表现人物性格、感情的方法,如果不继承下来,慢慢淡化,将来怎么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具体到古代诗词,语言凝练,有韵味,尤其旧体诗基础好的作家,像鲁迅、郁达夫、汪曾祺等,他们写的散文、小说就不一样,那种诗的韵味游走在字里行间,余味无穷。 羊城晚报: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与发展也面临一些难题和挑战。 黄天骥:这个问题现在恐怕难以解决。其实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追求和兴奋点,这是必然的,这样才会进化,所以过去的人对古代诗词记得比较多,现在的人只记得一部分,这是自然的。语言环境、社会环境都变了,对古代文学的态度也会发生变化。所以不一定要强求,顺其自然即可,我们做研究的告诉大家什么是好的,然后感兴趣的人自觉去学习就可以了。不过在继承的时候,千万别忘了“优良”二字,传统文化里也有不少糟粕,不是什么都要继承。要学会甄别和筛选,哪怕是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也并非全都是优秀的作品。 羊城晚报:现在很多家长学前教育都是让孩子背唐诗,您有什么建议? 黄天骥:小孩子背诵唐诗可以不求甚解,而且也没一开始就深刻理解的必要。你先背下来,再慢慢琢磨,这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太早告诉小孩子诗歌背后的意义,给他定了一个框框反而不妥。我知道现在中小学课本中的古代文学作品多了,要求孩子们背诵,这是好事,可以培养对古诗词的审美和语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