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复兴 每年的元宵节那天,老傅的姐姐都要早早出门去买元宵。那年月,没有冰箱,没有快递,元宵节吃元宵,必须得当天买,当天吃,真正遵循的是传统中的不时不食。 那时,卖元宵的店铺,也远不如如今这样遍地开花。很少的卖元宵的几家店铺,一清早会在门外摆出摊位,亮出摇元宵的大簸箩。早些年间,还没有机器摇元宵的,看人双手晃动着大簸箩,一个个小方块元宵馅,在簸箩里的江米面粉中,如同翻着跟头的顽皮孩子,将面粉一点点沾惹全身,滚成一个个白白胖胖的小雪球。摇元宵是力气活儿,也是技术活儿,大大的簸箩,小小的元宵,在一个人的双手之中,对比得那么醒目,摇元宵的师傅,是这大小之间的比例中项。 摇元宵的过程,像街头表演变戏法一样,很能吸引小孩子。排再长的队,排到了头,看到从大簸箩里摇出的元宵,送到自己的手里,仿佛长队的尽头开出了一朵朵洁白晶莹的花一样,让小孩子高兴不已。 老傅是我的中学同学,母亲、姐姐和他三人相依为命。姐姐大他几岁,为了替母亲减轻家里的生活负担,早早参加工作。每年元宵节那天,姐姐总要请上半天假,排队买元宵。老傅会像姐姐的小尾巴一样,跟着姐姐一起去,兴致勃勃地看着摇元宵的西洋镜,想着待会儿吃元宵的热乎劲。那时候,买元宵的队伍,长龙一样,逶迤甩出老远,不排上半天的队,还真的买不上。好不容易,买上元宵,回到家,姐姐要煮上元宵,煮好后,盛在碗里,先端给母亲,再端给老傅。请了半天的假,排了半天的队,为的就是元宵节让母亲和老傅吃上这一口。 老傅结婚有了女儿,每年元宵节,姐姐还是会一清早出门买元宵。这时候,跟在姐姐屁股后面的小尾巴,是老傅的女儿了。老傅的女儿看到,买元宵的队伍实在太长,姑姑那样有耐心,排着带拐弯儿的长队,买好元宵,送到奶奶家,煮好元宵,先端在奶奶面前,再给她盛上一碗。每次元宵节吃上这一碗元宵,她的心里都翻腾这样的想法:为了吃上元宵,姑姑也太不容易了;继而,又想,就为了给孩子大人吃上元宵,冷风天里,姑姑排这样的长队,值得吗?最后,她想,自己长大了,反正不会干这样的傻事、排这样的长队! 转眼,老傅的女儿长大了,仿佛一眨眼的工夫,就长成了当年姑姑为全家人排长队买元宵的年龄。元宵节又到了,传统的民俗,渗透进一代代人的血脉中,无法剔除,这一天还是要吃元宵。老傅的女儿,像当年姑姑一样,一清早也出去买元宵。和以前一样,买元宵的队伍还是那样的长,但人们的耐心也和以前一样恒定持久。老傅的女儿,排在长队之中,也和当年的姑姑一样耐心地等着。 如今,卖元宵的摊位,依然摆在店门外面,只是没有了摇元宵的大簸箩,元宵早就机械化批量生产,一车车送到各个销售点。等待买元宵的时候,少了师傅晃动着大簸箩的表演,长队的尽头没有了开出洁白晶莹的花的感觉。而且,跟在她后面的,没有了小尾巴。儿子上学,课业忙不过来,好东西也吃得太多,元宵,不那么吸引人了。 终于买上了元宵,老傅的女儿会把元宵拿回家,煮好,端给全家人吃。只是,奶奶已经过世三十多年,父亲也过世五年了,姑姑年过八十。但是,元宵节的元宵,还是要吃的;排长队买元宵还是要去的。尽管,这只是重复动作,却是这一天的规定动作。
-
即时新闻

排长队,买元宵
来源:羊城晚报
2025年02月18日
版次:A09
栏目:
分享到微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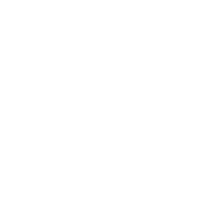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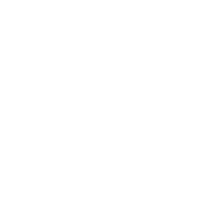
使用"扫一扫"即可将网页分享至朋友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