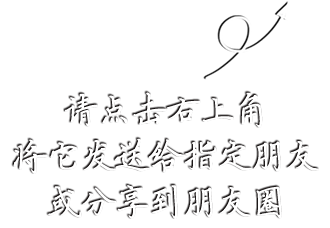□张金刚
若无檐溜,那静默的屋舍便少了灵动俏皮,失了情趣韵致。
雨来,或冰雪消融,积水汇流,乖巧地奔向瓦口,循滴水瓦尖,应房架之势,恣意滑下,甩出弧度完美的抛物水线,溅落在院石上,绽放朵朵水花,荡起圈圈水晕。一条、两条、无数条,绵延不绝,为光秃枯槁的屋檐垂下珠帘,配饰流苏,一时美艳起来。
即使由“哗啦”减为“滴答”,也只是由“豪放”转而“婉约”,虽淡了激情,更添了含蓄,饶有一番诗意禅味。抑或在严冬,水线少顷便凝成冰锥,冷峻封冻了柔情,然而却更令人期待融融的暖意渲染天地之间。
檐溜,我愿将其儿化为“檐溜儿”。虽“檐溜潺潺朝复暮”,以至“年复年”,流逝了年华,可无论何时何处邂逅,都如是初见,分外欢喜。亲切地唤一声“檐溜儿”,是新识,又似老友,瞬时亲近了几分,一如故乡老屋檐下的那一溜儿水、一溜儿冰、一溜儿光阴……
那几间老屋,再普通不过。突起的房檐上,不远儿一道瓦口带一片滴水瓦,不远儿又一个,六七个。瓦口处常生有几株倔强的麦芽、椿芽、豆芽,扒住可怜的浮土,随风飘摇,蓬勃着夏日的张力。怕檐溜儿过猛,淋湿了檐下,父亲会趴在瓦口处,伸长胳膊,给瓦接上一段铁皮或塑料瓶,将溜儿甩得更远。
春雨秋雨较为温和,滴下的檐溜儿少很多,弱很多。沥沥拉拉,滴滴答答,打在初生的嫩芽或将颓的秋叶上,也无多大动静。润物无声也罢,萧瑟苍凉也罢,于我少有触感。
而夏雨就不同了,骤雨、连阴雨常至,即便穿了雨衣,撑起雨伞,也难保不被淋湿。故而,一家人便聚在家里,哪儿都不去,倒也因雨得福,其乐融融。
雨不停下,檐溜儿便不断。水漫过屋顶,倾泻而下与庭院积水汇合,挟卷着枯草黄叶、豆荚麦糠、鸡粪垃圾,流向院外沟渠。这檐溜儿似一把大扫帚,替我干了清扫院落的活计,省了挨母亲的唠叨,一直让我心存感激,以至于常站在雨后清洁的院石上,冲屋檐作揖致敬。母亲以为我在敬天,附和道:“是该感谢老天爷,风调雨顺,庄稼有个好收成,饿不着咱!”
更多时候,是父母和我一起在檐下忙活。“哗哗”的雨声,檐溜儿敲打石榴、蜀葵、月季、丝瓜的“啪嗒”,或注入筲桶的“叮当”“哗啦”,是最悦耳畅快的伴奏。
此时,母亲常会为全家包一顿嫩南瓜、腌猪肉馅儿水饺,热乎乎地驱走雨天的凉意;或者手上舞动麦秸编草帽辫儿,穿针引线纳鞋底,缝补衣服。父亲则坐在蒲团上,归拢黍秸、扫帚苗、高粱穗,专注地绑着笤帚、扫帚、炊帚;或者拿出他的斧锯刨凿干会儿木工,操起他的板胡兴致盎然地拉上一段儿解闷儿。
那时的冬天,雪很多很大,厚厚地盖了满房、满院、满村。午后,初霁的暖阳与蒸腾的炉火令屋顶的积雪丝丝融化,雪水滴答,缓流,将瓦口下的雪堆钻出几道深洞。可傍晚或翌日,“瓦沟冻残雪,檐溜粘轻冰”,雪水檐溜儿变成了冰锥檐溜儿,映着灯光或日光,通透透、亮晶晶,似是屋檐生出了凌厉的冰牙,有些吓人,生怕被咬到。但我更愿视其为屋檐挂起了风铃,想抄起勺子铲子敲出一曲《铃儿响叮当》;视其为一把神奇的水晶篦梳,梳理着嘈杂蓬乱的农家日子。
登上梯子或凳子,敲下一根最长的冰锥,握在手中当宝剑,吸溜着“檐溜儿”般的鼻涕,与伙伴儿们打得热火朝天,棉袄“冒烟儿”。冷不丁儿,不知谁将宝剑顺着领口插入,激灵一下,打得更惨烈。渴了,宝剑当冰捧,舔几口或咬几口,爽爽地解渴。忽地想起一道传说中的东北硬菜:油炸冰溜子。是个啥味道、啥体验?是不是一口下去,外层酥脆香甜,里面冰凉脆爽,吃起来就像嚼冰棍儿一样,嘎嘣嘎嘣,冰火共生,想想就过瘾。
当冰雪融水,水又结冰,相融相生一季长冬,檐溜儿渐渐消了踪迹,便又是一个暖春。
而今,那老屋已倾颓,只留一堆瓦砾。我徒手刨出几片弯瓦、两片滴水瓦,上面还接着铁片。看着,品着,恋着,最后高高举起一片,高至记忆中的屋檐处。那尖尖的瓦尖儿似有檐溜儿生成,滑下,滑入我的眼;再从眼眶溢出,形成温热的檐溜儿,顺着中年男人脸上的沟壑,滴在院石上,滴答,滴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