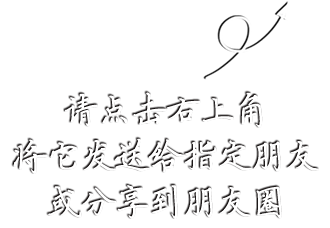□倪西赟
钢笔
我拥有一支几十年的天蓝色钢笔,它尖尖的脑袋,胖乎乎的身子。
年少时,拥有一支钢笔,是何等威风、神气!
把钢笔插在我的上衣口袋,步伐有力,腰杆挺拔!
每天,变着法子,让钢笔吸饱黑色、红色、蓝色、绿色、黄色等不同颜色的墨水。
我把字迹款款落在稿纸上,我把我的大作,邮寄给编辑。
我有时候还会微微皱起双眉,轻轻翕动鼻翼,给我喜欢的女孩,写一张纸条,说:“我喜欢你。”
那些年,钢笔是我的密友,是什么时候和它开始生疏的呢?已记不起。
而今,那支蓝色的钢笔就放在我的电脑旁的笔筒里。我在电脑上飞快打字时,它就在旁边看,什么也不说。
虽然不经常用钢笔,但是我却有个习惯,每天把蓝色的墨水瓶打开,让钢笔喝饱墨水,在白纸上写上几个字或者画上几个圈,笔尖流畅,随心所欲。
很多东西迅速崛起,又有很多东西悄悄落幕。我们不得不与时俱进,但有些东西,却让人怀念。
写信
乡下的父亲,至今还执着地,每个月给我写一封信,平邮。
信的每次开头,都是“见字如面”!
父亲的信,不够凝练,洋洋洒洒,少则三五百,多则三五千。
父亲的信,没有主题,东扯西拉,来回重复。
父亲的信,没有新意,鸡鸭鹅,牛羊马,土坷垃庄稼。
我曾劝父亲不要写信,用电话和微信方便。
父亲却说,电话里一下想不出说啥,微信视频,感觉像面对面说话,太近,不够亲近。
不管我同不同意,父亲按月准时给我写信。
我慢慢看懂了父亲的信,父亲的杂乱无章里,其实是一种执着:我从未离开他。
花香
养了几年的茉莉花,今年才发现,茉莉花白天开得缓慢,但天黑以后,攥了一天拳头的花苞,轻轻舒展。只是花开短暂,黎明时,茉莉花已经开败。
一天晚上,在阳台上,像装了一瓶子的茉莉花倒了,茉莉花的香洒了出来,在空气里弥漫。
老婆用鼻子嗅一嗅,说了一声“好香”,便不再理会;我也发了几声赞叹,便没了下文;孩子跑到阳台摘了两朵茉莉花,在手里玩了两下,丢弃了。
只有母亲,拿了一个板凳,去到阳台上。她坐在茉莉花的旁边,一脸的陶醉。
我问母亲,您是在守花香?
母亲笑笑说,不,我不做什么,就是坐在它身旁,陪它一会儿。
世上很多事情如花香,留不住,但可以陪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