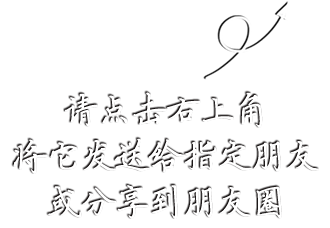□何万明
一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时光飞逝,岁月流转,辞旧迎新,转眼间,充满希望的2023年如期而至。
要说对过年有什么印象?我觉得还是童年时代的感觉比较美好,自然就印象深刻,因为其时年少,过一年就是长大了一岁,而小时候非常盼望长大,歌曲《童年》就是这样唱的:“什么时候才能像高年级的同学有张成熟与长大的脸?盼望着假期,盼望着明天,盼望长大的童年……”童年时代盼望过年,除了想快点长大,还有个重要原因就是过年有吃有玩有新衣服穿,小孩子嘛,想法都很简单纯粹。
我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初,记忆中小时候每家每户都有养猪,通常是年初买来猪崽,平时就用剩饭剩菜喂养,还有就是我们小孩子去野外打来猪草煮烂作为猪食。由于缺乏营养,猪长得慢,通常养了一年能长到一百多斤就已经相当不错了,年底大家就把自家养的猪请屠户来宰了。进入腊月二十五,猪的末日就到了,直到年三十,每天早上猪的惨叫声、哀号声此起彼伏,让人听得心惊肉跳。此时村里很多狗也会跟着狂叫起来,显得焦躁不安,甚至躲到野外去,几天不敢回家,真是“兔死狐悲,物伤其类”。
如果有的人家猪没养大,想年后再卖,就会提前向劏猪的人家订购过年的猪肉,通常一家有六七口人,就订购10公斤左右,节约一点可以从除夕吃到年初七、初八,一个春节就过去了。现在想来,当时大家养猪的目的相当于现在银行的零存整取,年底杀了猪除了留一些给自家过年,大部分都卖了,所得的钱用于年后孩子上学、购买化肥农药等开销。所以很多人家一年到头的收入就寄托在猪身上。万一发生什么意外,比如发猪瘟死掉了,那就惨了。又或者有的人家不会养猪,把猪养得只长毛不长膘,没法劏,那这个年肯定过不好,因为要为过年和年后的开销发愁。
通常,离除夕还有十天左右,大家就进入过年状态,开始准备年货了。那时候的年货,主要是指吃货(不是现在表示喜欢吃各种美食的人的意思),因为除了吃的,其他东西几乎没钱购买,而且,吃的东西大都是自己做的。记忆中大家准备的年货无非是用面粉或米粉煎炸出来的各种食物,比如糖环、开口枣(用面粉加红糖揉捏成中国结或青枣模样再进行油炸)、脆枣(用面粉包着花生米再进行油炸,香脆可口,故名),还有爆米花,等等。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有个堂姐在外面学会了做油角子,形状与北方人爱吃的饺子一样,油角子的馅料是炒熟的花生米碾碎后加上芝麻和白糖,用饺子皮包成饺子形状再放到油锅里炸,非常香甜好吃,咬一口,从嘴里甜到心底,因此很快就在我们大队传开了,然后又传到别的大队,甚至别的镇。我的母亲勤劳善良、心灵手巧,堪称客家农村妇女的典范,虽然那时候我家还相当贫穷,但她总能变戏法似的做出很多年货,让我们一家人过个快乐年。
二
民以食为天。过年最大的吸引力就是每家每户都拿出所有家底来犒劳自己的肚子。在我的家乡,过年有几道令我们回味无穷的特色菜,譬如肉圆、香芋扣肉、猪骨头炖莲藕、酿豆腐,等等。肉圆,也许大家听起来有些陌生,其实就是常见的肉丸,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东西,只是叫法不同罢了。家乡的肉圆配料很精致,主要有猪肉、鱼片、香菇、冬笋等,各种配料放在砧板上一起剁烂,加入食盐充分搅拌,再捏成乒乓球大小形状,盛在盘子里隔水蒸熟,就成了一道色、香、味俱全的美味佳肴。
为何叫肉圆而不是肉丸呢?我想这可能跟汤圆不叫汤丸一样,主要是取其团团圆圆的寓意吧,更何况“丸”字有“药丸”的意思,不吉利。旧时,家里的男人通常一年四季在外面谋生,只在年底才回来与家人团聚,所以年三十晚上一家人围聚在一起,吃上一顿热气腾腾的肉圆,就显得特别有意义,我估计这跟北方人大年三十想尽办法都要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包饺子、吃饺子意义等同吧,只是表达的形式不同而已。
从我记事起,几乎每年春节家家户户都会打肉圆。我们那个村子比较大,有上百户人家,每年大年三十那天下午,乡亲们在砧板上剁肉馅的声音就会从每家每户的厅堂或者厨房传出来,此起彼伏。我的父亲还可以双手同时拿起菜刀左右开弓,剁得抑扬顿挫,让我们既享受音乐之美,又充分感受到一种温暖、温馨、祥和的节日气氛。
记得那时候大家都会在晚饭前把肉圆蒸好,先蒸好的人家必定很热情地邀请左邻右舍过来品尝,大家拉拉扯扯的,虽然或许有些做作,但让人感觉到浓浓的乡情。现在生活好了,绝大部分人家都住上单家独院的楼房,过年打肉圆的习俗依旧保留着,但拉拉扯扯邀请邻里来品尝的现象却似乎很少见了,我想应该是因为现在吃肉圆再也不用等到过年,平时想吃就可以吃了,不再觉得有什么稀奇,就好像现在虽然很多地方还保留着过年穿新衣服的习俗,但因为生活富裕了,平时也可以随时买新衣服穿了。
三
对于孩子们来说,过年除了吃喝玩乐,还有一个令人欢欣雀跃的节目就是探亲,也就是走亲戚。我现在觉得以前探亲除了通过走访增进亲情外,还有一个目的也是吃喝,而且是吃别人家的。客家人都很好客,通常都会把自己舍不得吃的好东西拿出来招待客人。
记忆中我们经常去的一家亲戚是我奶奶的妹妹家,虽然也是在同一个镇,但是要翻过几座山。印象中通常是年初五前后吃完午饭,奶奶就会带着我和姐姐出发了。早春的天气还非常寒冷,我们祖孙三人行走在山坳里的青石板路上,除了呼啸凛冽的山风和 “沙沙沙……”的脚步声,没有一点声音,当真是“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但我们似乎不曾害怕过。然而,记得有一次,我们从姨婆家吃完午饭回家,不知何故,居然在山坡上迷了路,一直在转圈圈,就是找不到路,其时夜幕就要降临了,我奶奶很焦急,不停地喃喃自语:“怎么会打倒桩呢?”我们姐弟俩也很害怕,在山上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后来究竟是怎么回到家的,早已不记得了,毕竟40年过去了,只是现在偶尔想起还心有余悸。
记得当时我姨婆家人丁很旺,她生育了好多个子女,有个大我十多岁的表叔腿脚不太灵便,但却是个能工巧匠。他会用竹子编织成簸箕、箩筐、竹椅、鱼篓等用具拿到镇上卖。通常,我们在她家好吃好喝了一两天,奶奶就带着我们打道回府,尽管姨婆再三挽留我们多住几天,但精明的奶奶知道亲戚家是用来探访的,而不是用来长住的。我和姐姐虽然乐不思蜀,但也只好听奶奶的,不过,每次我们回家,那个瘸腿的表叔都会送几个鱼篓给我,让我非常开心。
人世匆匆,一眨眼我就离开家乡30年了,平时也只是在清明节才回去祭拜父母,然后又匆匆忙忙回到惠州市区,因而极少去探亲访友。没有父母的故乡,我就是一个过客啊!我好几次对我姐姐说,希望找个机会再去走访昔日的那些老亲戚,重温儿时那种温馨的感觉,我姐姐也满口答应到时一定陪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