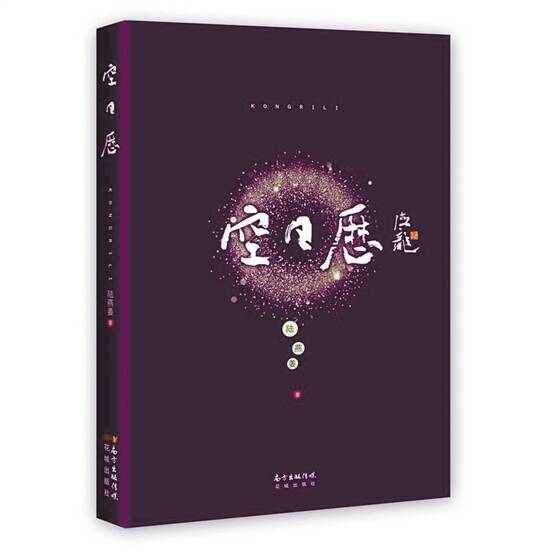
|
|
|
不妨先从这部诗集《空日历》的集名说起。在我看来,“空日历”事实上包含了三个元素:显而易见的,当然是日历以及隐身其后的时间。日历是对时间的捕捉和刻写,日历是时间的具身化,时间通过日历而显形,获得了坐标和刻度。时间是空漠辽远浩浩荡荡的一片空,日历为这片空赋形,给它坐标系和路线图。有了日历,时间一定程度上被驯服而成了人的时间。当然,日历描述洞察了时间,却不可能阻挡住时间。所以,日历其实是文化把握时间的一种方式。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独特的时间观,每个民族也有各自独特的历法。这个意义上的日历是公共的,它从属于一种民族的集体智慧。显然,日历对时间的把握是文化的,却并不是诗的;所以,日历不是诗,但“空日历”却可能是诗。我把“空”理解为清空,理解成一个动词,在象征的意义上,“空日历”代表着诗人以个体的想象力疏离于公共的文化秩序,从而创造了诗的可能。 诗人毕生都在寻找着一种有效的语言。对于文化来说,公共语言作为载体已经足够。文化需要进行的是内容生产;但对诗歌来说,一直有一种尚未说出的东西,期待一种有效的语言把它发掘。齐泽克说:“我们感到自由,是因为我们缺乏一种语言来表达我们的不自由。”这意味着,语言不是容器式地承载内容;语言劈开隐匿事物的外壳,让光照亮,让大地敞开。发明语言,就是发现世界。我在这样的意义上理解想象力突围之于诗人、之于世界的意义。维特根斯坦说:“语言的边界就是世界的边界。”公共语言为我们提供了社会群居的语言屋舍,人们居留于其间,获得庇护,也受到某种想象力藩篱的囚禁。公共语言建制必然以其稳定性限制生存向开阔和幽微处发展,因此,诗的想象力就是解放我们日渐格式化生存的力量。 《空日历》是诗人陆燕姜的第四部个人诗集,它继承了陆燕姜写作上一以贯之的瑰丽想象和独特修辞,陆燕姜正是以诗性想象力不断刻写时间、解放刻板生命的诗人。“翻过一个日子,我/对昨日的行程轻吹一口气/装进收藏夹。腾出/辽阔的空白”(《空日历》)陆燕姜善用拼贴,好的拼贴让词在创造性相遇中如闪电洞开了沉沉夜幕,旁人那里简单如流水账的“日子”在她这里必须匹配以“翻”山越岭的动作,于是,一个“翻”字就洞开了日子内部沟壑纵横、千山万水的内质。值得注意的是,“翻”既是翻日历的翻,也是翻山越岭的翻。所以,当她赋予米粒般日常的日子以辽阔内质的同时,并不是任意为之,而是精心地寻找着词的桥梁和衔接。“翻”字把日子由小变大,而“对昨日的行程轻吹一口气”的“吹”则把漫长曲折的事物轻巧地化作一根羽毛、一张白纸。这段诗两个动词显出了诗人在事物内部腾挪跳跃的语言魔术。显然,这里不仅是简单的语言技艺,也显出诗人对生命的理解和了悟。凡人过日子就是过日子,诗人在语言魔术的辅助下,可以在日子中掏出山高水长,也可以将惊涛骇浪的一切压缩、清空,重新面对辽阔的空白和空白的辽阔。 诗人的想象力让他可以上穷碧落下黄泉,也能发现简单事物隐藏着的灵魂故事。比如这首《两只鸡蛋》:两只鸡蛋,躺在灶台上,静静地/肩负重任。准备赴汤蹈火/去捂住一个刚刚失去体温的人的嘴/让他从此不能与亲人说一句话/带着人类守口如瓶的秘密到达另一个国度//鸡蛋被打碎放进砂锅/无需搅拌,它们便化为一团/黄和白,两颗躺着的硕大眼泪/仿佛正上演的一场生离死别/生的灵魂抱紧死的肉体 两个鸡蛋,多么日常朴素的场景。陆燕姜却深入进去,挖掘了鸡蛋的灵魂叙事。短短几句中,赴汤蹈火的鸡蛋,不省人事的人,焦急期盼的亲人,还有人类那不能说出的秘密,这是一个多层次的命运故事;如果说第一节鸡蛋以他者的身份进入了他人的命运,第二节的鸡蛋则以皮绽肉裂的破碎深入了自身的生命底部。陆燕姜的想象力使“两只鸡蛋”这种朴素如歌谣的意象释放出现代诗滚烫驳杂的诗意。 丫丫既能够从词、意象中挖掘诗意,也擅长通过场景植入想象力。比如这首《出窍》:那个人骑着快马,从我身边呼啸而来/一手接住我的软腰,掳掠上马/而后疾驰远去//尘沙满布的大路上/只剩下脱了壳的影子/待在原地//她坚持住。坚持不哭出声/尽力搜寻那个马贼的所有信息/身材,发型,面相,服饰/左臂上的刀疤和棕褐色的牛皮马靴//后来,影子抱膝蹲下/泣不成声 这是一首以场景性和叙事性来展开诗意的作品。第一节用第一人称“我”视角,有趣的是,这与其说是一个在场的“我”视角,毋宁说是一个回忆性的“我”视角。“我”被席卷掳掠的当下,怎可能目击掳掠者“疾驰而去”,可见从这句开始,“我”分裂出另一个角色,一个观看者的角色在静观着亲临者的角色,这大概是第一种“出窍”;诗歌的场景具有非常强的想象性,这个戏剧性的场景很难说不是一种精神投射,所以,这个场景本身乃是写作者精神的漫游,这是第二种意义的“出窍”;我们还看到,诗中影子构成了对肉身的“出窍”(只剩下脱了壳的影子/待在原地),“我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而黑暗会吞噬我,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无论是李白还是鲁迅在影中投射什么样的精神内涵,影/身的关系并不曾“脱壳”。陆燕姜别出心裁地让身远去,而影子独留下。在我看来,这首诗在影/身/她之间缔结一种弗洛伊德式的精神结构:身像是那个重视本能快乐的本我,所以身渴望呼应着马贼的掳掠;影子却是那个不愿被欲望掳掠的超我,它居留于原地,忧心忡忡,而她是那个手忙脚乱调停本我、超我的自我,所以,“她坚持住。坚持不哭出声”。这首写出了现代主体的分裂出窍的精神症候,诗人在场景营造中拓展精神景深的能力令人称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