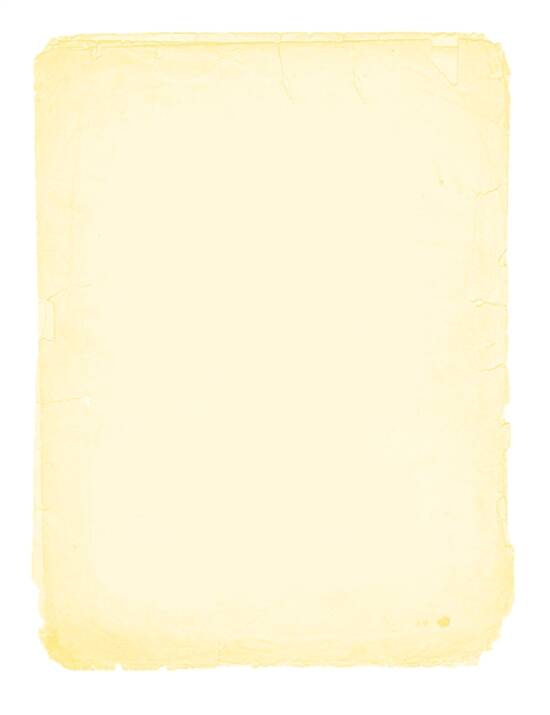
|
|
|
2019年清明节前后,我回到湖北省麻城市最北面、也是大别山南麓的福田河镇杨家河小山村,整修加固了百多年历史的老宅子。在昏暗潮湿的老宅子里,存放着几代人曾“刀耕火种”的各种农具和器皿,最多的物件是油光发亮的上釉大缸,估计有一、二百年的历史,称得上是我们家族中的“古董”了;其次,最多的便是几代人用过的钎担和扁担。看到钎担和扁担,便勾起了我儿时的记忆。 钎担一般是用笔直的柏树刨光皮、晾干打磨来做的,大概长1.8米、两头用尖尖的铁皮包裹着,主要用于挑柴火、稻谷与麦子的草把,粗一点的钎担能挑三百多斤的柴火,细一点的钎担也能挑一两百斤,它是农村里最为常见的劳动工具,也是家中数代男人担负起兴家责任的最主要农具。可以说,一个家庭的兴旺与发达改变,大部分是靠钎担“挑”出来的;有的家庭用钎担“挑”出了儿孙满堂、富贵吉祥、幸福绵长;有的家庭用钎担“挑”出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和美好的未来。 我父亲是个无师自通的木匠,给自己打造了多根钎担。在我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他专门给我也精心准备了一根钎担,仅钎担的重量就有十几斤。 钎担做好后,他带我去十几公里外的大山上砍柴。十岁的我,嫩稚的小肩上扛着一根大钎担,开始觉得很新鲜,觉得自己长大了、有力气了,“长本事了”、“很了不起”;走着走着,就蔫了一半,穿着破鞋子,用草绳捆住,脚上已磨出几个泡,走路蜇得生痛,一瘸一瘸的,觉得肩上的钎担也越来越沉。 到了大山上,看到很多干柴火,拣起来堆在一堆,把它捆成两大捆,父亲用钎担铩进去,扶在我肩上。我挑起来就下山往回走,走不到两里,感觉挑不动了,歇了一会儿,口干舌燥,跑到小河沟,趴下痛快地把山泉喝了个饱。 父亲挑着柴火往前走,叫我跟上;跟着跟着,慢慢见不到父亲的背影了,我又停下来歇口气,趁机抽掉几根棍子,减轻一下重量,接着又去追赶父亲。 大概走了五、六里,父亲也在前面停下来歇气,顺便等我,见到我满脸通红、大汗淋漓,父亲递过来已是湿透了的白大布毛巾,让我擦把汗。擦完汗,我再细看父亲的钎担上,一头大概有一百多斤一捆的柴火,两边加起来,起码有二百六十多斤。他起身挑起来的时候,只见钎担两头朝下耷,发出“吱、吱”声,走起路来时,“吱吱嘎嘎”响个不停,韵律感十足。 我跟在后头,也想找到“吱吱嘎嘎”韵律感,无奈我的钎担硬邦邦的,发不出任何响声,步履也找不到节奏。直到现在,我才明白,挑的东西太轻,钎担是“不高兴”的,它是不会唱歌的。父亲能够让钎担“唱歌”,唱的是负重之歌,也是一家人的“希望之歌”、“幸福之歌”。 在蜿蜒崎岖山路上跟着跟着,我又渐渐看不见父亲的背影了,害怕、疲倦和无助一齐袭来,我陡然啜泣起来……在荒野里哭泣没人理,也没有用,除了几只乌鸦在树梢上“看热闹”叫个不停外,还有就是一阵又一阵的凄厉风声。这个时候,我对钎担产生了深深的畏惧和恨意,怪父亲把钎担做得这么“硬朗”、“结实”,“沉得”使我白嫩的双肩像擦了红汞似的,一阵又一阵地发烧。在离村子还有五里的地方,爷爷突然出现了,他是专门来接我的。回到家中,爷爷用秤一称柴火,还有48斤;如果加上钎担重量,就有六十多斤了;如果不是在路上“卸负”,恐怕整担柴火七八十斤重了。 上世纪八十年初期,我到了十五六岁的年纪,已经能够轻车熟路地使用钎担了,也能够像父亲一样上山砍柴,挑一两百斤的柴火。作为家中老大,我用钎担承担了父亲的一部分责任。高一、高二读书期间,我的学费和给学校上交的每学期380斤柴火任务,都是我自己用钎担完成的,没有给父亲和家庭加重负担;那时候,一百斤活柴挑走三十里路卖九角钱…… 如今细想,我今天的幸福生活不正是那时用钎担“挑”出来的吗?没有钎担的“压榨”与磨砺,没有钎担的“鞭策”与敲打,就没有改变命运的强烈渴望。从这一点出发,我要感谢严厉的父亲!还要感谢“沉默无言”的钎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