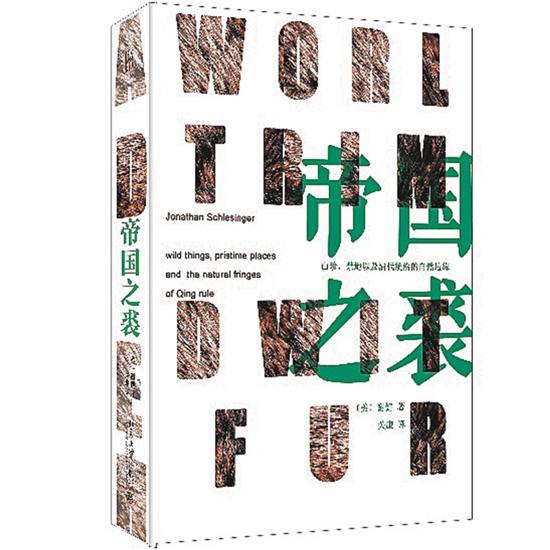
|
|
|
□谢 健 在清帝国,服饰、物质文化与个人的身份密不可分;不能把人和毛皮分开。服饰和肤色、脸上的痘癍一样能够代表整个人;缉拿逃奴、逃妻、逃兵时使用的标准“年貌单”通缉令综合了对人的生理和服饰的描述,仿佛一个人的外貌永远不变一样。根据法律,要“据体貌服饰缉捕”逃亡者。在斗殴中,不得打掉他人的帽子(或揪掉流苏)。如果一个外地人死在蒙古地区,他的尸体和衣服都会被送回原籍。这是因为服饰能够代表人的身份,而毛皮尤其象征了满族人的身份,推而广之,它还象征着边疆地区。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将很多隐喻赋予穿着毛皮的野蛮人。一如安东篱(Antonia Finnane)证明的那样,在整个帝国时代,穿着毛皮的野蛮人的形象在边疆文学中反复出现。司马迁把匈奴描述成“衣其皮革,被旃裘”,唐代诗人刘商(8世纪)在他的《胡笳十八拍》中叙述了汉代贵族女性文姬被迫远嫁匈奴的悲惨命运,作者借文姬之口哭诉道:“羊脂沐发长不梳,羔子皮裘领仍左。 狐襟貉袖腥复膻,昼披行兮夜披卧。” 自建立金朝的女真人控制中国北方之后,南宋的文人同样把毛皮和他们的对手女真人及后者的残暴行为联系到了一起。蒙古人灭金和南宋之后,文人们又把前者与毛皮联系到一起。匈奴、契丹、女真、蒙古、满洲都差不多:他们都买卖这种毛皮商品。 确实,汉人精英也穿毛皮,历史学家能够撰写一部与内陆亚洲平行的汉地毛皮风尚史。例如,在战国时期有两种官帽包含了貂皮元素:一种是貂蝉,一种是珥貂,这两种帽子都以悬挂貂尾为特色。传统文学告诉我们,貂蝉是赵武灵王发明的,这是他建设团队精神的一个环节:“胡服骑射”是那个时代的口号。貂蝉一直流行到唐帝国,薛爱华(Edward Schafer)注意到这种帽子“是仗剑出塞,或者是返回故土放鹰走狗的任侠少年的特殊标志”。 同样,从汉朝开始,历代史家都忠实地记录来自东北的贡品,以展示毛皮如何象征汉人帝国的权力。大众对毛皮也有特殊需求,特别是蒙古人统治汉地之后。明初,蒙古文化对汉人的时尚颇有影响。例如比甲(一种长款背心)、质孙(单色朝服),以及所谓胡帽。1430年,朝鲜王廷注意到“土豹貂皮,中国之人以为至宝”;朝鲜宫廷本身也很快要求最高级贵族戴貂皮护耳帽,其他人用松鼠皮。时尚和物质文化超越了政治和族群边界;穿得像野蛮人并不一定就会变成野蛮人。 消费者对毛皮的了解逐渐增加。李时珍(1518年-1593年)在对貂皮进行了一番研究之后,在《本草纲目》中描述道:“用皮为裘、帽、风 领,寒月服之,得风更暖,着水不濡,得雪即消,拂面如焰。”李时珍以医生的身份建议大家用貂裘的袖子擦去眼睛上的尘土。他的书里还列举了其他毛皮动物,如海獭。作者注意到:“今人以其皮为风领,云亚于貂焉。”毛皮在京师实在太风行了,以至于朝廷于1506年发布了一道禁奢令,禁止奴仆、妓女和底层人穿貂裘。一个世纪之后,某些战略家向朝廷发出警告:毛皮贸易是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崛起的基础。 对于其他思想家而言,毛皮最大的危害是它贬抑了汉文化。在1491年3月6日的一份令人吃惊的档案中,某位御史警告朝廷,京城男女“胡服胡语”、汉人像“胡”一样穿着貂皮狐皮。他要求“复华夏之淳风”,还敦促朝廷“扫胡元之陋俗”并实现“习俗纯正”。汉人穿毛皮,但穿毛皮并不是汉人的习俗。为了肃清外部文化影响并恢复传统风俗,一切异族服饰,特别是毛皮必须被摒弃。所以,如果满洲的毛皮时尚是一项政治计划,那么汉人的反弹就与此同理。二者都从自己的角度建构出了一种永恒、原始的淳朴风俗。 因此,清朝统治全国之后,毛皮仍然是一个争议点。谈迁在《国榷》中记载,他于满洲人定鼎十年之后抵达北京,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全新的、恐怖的世界。在顺治帝的万寿节中,他记载礼部官员如何花费一周的时间穿着貂皮或狐皮举行庆典。对于谈迁而言,这种衣服足够让一个贫寒官员破产:“闻上御玄狐裘,直三千金。诸臣玄裘最下者千金。”但是大家对这种浪费束手无策:穿毛皮是新规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