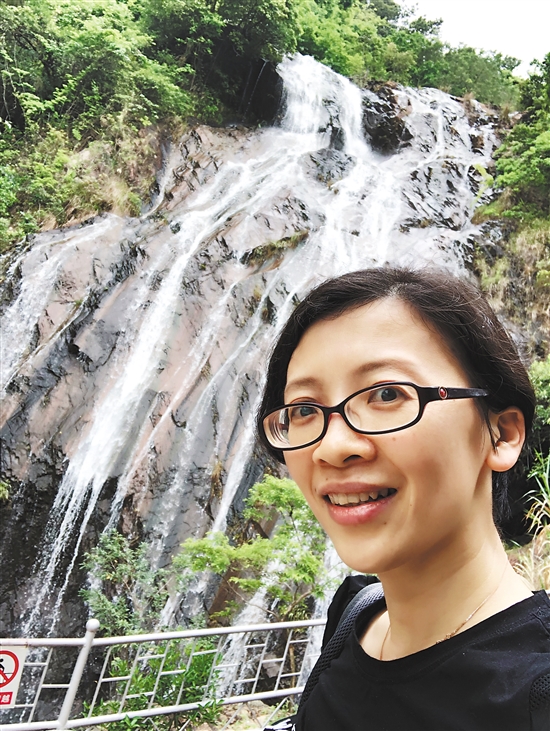
|
|
曾玲玲 |

|
|
郭学雷 |

|
|
周京南 |

|
|
陈文敏 |

|
|
铜胎画珐琅花卉纹杯碟 广州博物馆藏 林清清 摄 |

|
|
“白加白”白釉广彩连枝花卉徽章纹瓷盘,广州博物馆藏 林清清 摄 |

|
|
1776年两广总督李侍尧进贡的珐琅复合器的大象 林清清 摄 |

|
|
广彩在不断传承创新 陈文敏供图 |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林清清(除署名外) 受访嘉宾(受访者供图) 受访嘉宾 曾玲玲 广州博物馆副馆长,文博副研究馆员。专注于对广州城市史、清代外销艺术品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与策展,主持“瓷路相逢——清代外销瓷的中国元素与西方情调”、“苏州样广州匠——苏广明清工艺精品联展”等专题展览,出版专著《瓷话中国——走向世界的中国外销瓷》、《广州西关印记》等 郭学雷 深圳博物馆副馆长,研究馆员,中国古陶瓷学会理事,广东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深圳市博物馆协会会长,复旦大学兼职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展览策划与古陶瓷研究,曾主持“官钧”瓷器、金元红绿彩瓷器、吉州窑与黑釉瓷器等多个重要展览及学术研讨会,研究涉及钧窑、红绿彩瓷、吉州窑、磁州窑、黑釉瓷、山西陶瓷、元明青花、广彩及中外陶瓷技术与文化交流等领域 周京南 故宫博物院宫廷部研究馆员,古典家具研究专家 陈文敏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广彩”代表性传承人,广东省工艺美术研究所研究员,广州莲花陶瓷实业有限公司艺术总监。孩提时受容庚、商承祚等辅导和启蒙,师从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余培锡。代表作被故宫博物院及多家博物馆收藏 曾经被誉为“金山珠海”,是皇家的“天子南库”的广东,工匠们的匠心巧工,不仅带来了宫廷内的“洋货热”,带来了成为欧洲生活时尚的“中国风”,更带来一个时代中西贸易文化交流的繁盛。广彩、珐琅、广式家具、广绣、牙雕……事实上,在中国传统工艺的艺术价值与渊源架构中,“广作”都有重要影响和地位。 目前正在广州博物馆展出的“匠心神巧——广作特展”,由广州博物馆联袂故宫博物院、北京市颐和园管理处、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汇聚四馆所藏103件(套)清代至当代广州工匠制作的钟表、牙雕、陶瓷、珐琅、家具等广作工艺精品。这场“广作”精彩大秀,开展一个月来,突破了广州博物馆近20年节假日单日观众量最高纪录,国庆期间单日入馆人数超过14000人。 除了让观众们近距离感受到两百余年间广州匠人的匠心奇思与巧夺天工,展览中,首次提出了“广作”这一概念,将分散的广东工艺美术、非遗传承各个单项整合起来,将“广作”概念带到了更高的学术研究层面。深圳博物馆副馆长郭学雷,在此展中首次发表自己关于 广珐琅与广彩渊源的课题研究成果;10月27日,故宫研究员家具专家周京南在广州博物馆开设清宫收藏广式家具特色的讲座,观众反应热烈。对“广作”的全方位研究,由此更系统化。 仅仅是名字的改变,会否带来学术研究、收藏地位上的改变?文化影响力会有多大?羊城晚报记者请来博物馆长、故宫专家以及广作代表之一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从不同角度来探讨。专家们向羊城晚报记者表示,“广作”并不是将广州传统的工艺美术简单集合。经过系统梳理,重新认识“广作”,才能重塑“广作”在艺术价值和收藏市场地位上的影响力。 壹 “广作”大秀 为何观众热度专业度双爆棚? 羊城晚报:“广作展”引发参观热潮,观众人数突破纪录,原因为何? 曾玲玲:广州的本土工艺早在汉唐时期就初露锋芒,发展至明清大放异彩。广州工匠凭借天时地利人和,不断结合西洋技艺创造出自成一派、大放异彩的“广作”工艺品,赢得皇室、民间、西方商人的青睐。比如汉朝就有的广州牙雕,到乾隆时期与江南牙雕、宫廷牙雕并称为中国牙雕三大流派。而广绣,早在唐代就已有相关文献记载,至清末民初,广绣与苏绣、湘绣、蜀绣并称为四大名绣。 到了当代,广州的手工艺还遗留下哪些?我们希望能对清代以来“广作”的发展历程、工艺水平、艺术价值有一个立体的呈现:既有作为外销品蕴含的东西技艺、文化交融,又有本土民间使用的情怀记忆,还有宫廷收藏广作体现的不惜工本、华丽精美、巧夺天工。所以此次展览持续至明年1月5日,展品数量之多、品类之繁、级别之高,应该也算历年广州举办同类展览之最。比如第一展厅的大柜子,一对珐琅复合器的大象,是1776年两广总督李侍尧进贡的。200多年前不知道花了多少人力物力成功烧造再顺利运至紫禁城。而科技物流发达的今天,我们再把它们安全运回来也花了三天两夜。 羊城晚报:此次“广作展”,首次将“广作”作为整体概念提出,是否有助于对“广作”的研究开发和发挥文化影响力?是否已有跨门类或跨馆合作的研究项目? 曾玲玲:清代有“广木作”之称,指清代广州制造的家具,但以往对于广州工艺广府,并没有明确提出一个整体的概念。我们觉得,无论是广州制造或者是广府制造,似乎都不能全面呈现广州工艺的特色和影响力。我们在提出这个概念前,也与广州和苏州文博同行、故宫专家反复讨论。最终认为,此次展览提出“广作”这个概念,是为了集中梳理、呈现广东工匠的历史源流、艺术价值。属于更多地从学术角度提出的一个概念。 我们通过对前期许多材料的整理,去探讨这个概念,会发现许多“广作”工艺之间,存在相互影响,比如珐琅和广彩的关系;比如清代宫廷的广式家具,镶嵌着象牙、珊瑚、珐琅和玻璃画;广州的外销扇,它也是有不同材质、工艺的复合。这些“广作”手工艺之间,是互相合作,也会形成更有创造力的新的作品。 郭学雷:广州作为一个对外开放的地方,它肯定不会只有单一工艺见长。如果从一个宏观的艺术史的角度去观察,可能会对广作这套系统有更丰富和深层次的认识。正如我现在研究广珐琅与广彩的渊源,也是源于我研究纹章瓷断代时一些发现。 比如我曾接触到荷兰国立博物馆的一件重要器物,它上面写有:“甲辰花朝写于岭南珠江精舍”,说明它是在广州画的。落款的唐金堂,经我翻查,是一位大概从康熙末年、雍正到乾隆时期的珐琅名家。广珐琅有一种典型的课子图,很可能就是他画的,因为那件东西是雍正二年的。一些关联性的节点能够打通,你就知道唐金堂可能在康熙末年已成为了广珐琅名家,艺术水平极高。以前不知道,在康熙末年广珐琅就能达到这种艺术高度。这就能还原一个器物原本那个时代的地位和艺术成就。 贰 曾经辉煌 “广作”地位如今是否被低估? 羊城晚报:“广作”的艺术价值与市场地位,是否被低估? 曾玲玲:“广作”中的外销品部分,经过了这十来年国内外博物馆的研究和展示宣传,现在大家对它的关注度还是很高的,而且由于收藏风气影响,回流的也比较多。而皇室宫廷收藏部分,毕竟来源有限,目前以博物馆收藏为主。 但如果说艺术价值,与世界同时期水平相比,还有很多尚待挖掘之处。例如此次广彩展品中有一件雍正的“白加白”,就是在白色的瓷器上,用白色釉料画了透明的白色花纹。这个工艺是17世纪意大利发明的,但是在雍正年间就已经传到广州并被广州工匠掌握。另外广州博物馆近年征集最具研究价值的纹章瓷是英国的奥奇欧佛家族定制的,当时为了定制这批纹章瓷,专门请了当时英国一个有名的画家,在木板上画好定制的图案,带来广州,而广州工匠几乎是百分之九十几的高还原度。当时订购的价格就是一般纹章瓷的十倍,日用瓷的百倍了。所以同时兼具学术和审美的价值。 羊城晚报:在古典家具领域,广作家具一直具有重要的地位。在清宫造办处有“广木作”,与苏作京作匠人一起,为清代皇家打造家具器用。广作家具的地位与收藏价值,在宫廷收藏体系中,有何体现? 周京南:清代皇宫对于广式家具特别喜欢,在清代宫廷紫檀家具中,保守估计至少有五分之一是广式风格的,包括宝座、插屏、柜格、佛龛,甚至有皇帝的婚床。清帝同治十一年大婚典礼时,曾交粤海关备办硬木雕龙床。这些都在我查阅有关档案时有所发现。 在存世于今的清宫家具中,可以看到有很大一部分家具,是受到岭南地区广东家具的影响,用料考究,造型厚重,装饰风格华丽精美,中西合璧,具有鲜明的广式家具的风格。清代宫廷中广式家具,在中国家具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页,占有着重要的地位。 羊城晚报:各种“广作”元素的交织,对广式家居的发展有无影响? 周京南:在宫廷收藏中可以看到,广式家具中有许多“广作”技艺交织。比如宫廷收藏的广式家具中,还能见到大量玻璃油画、珐琅技术以及受西方建筑雕刻影响的装饰纹样。 例如玻璃油画明末清初由西洋传入中国,首先在广州兴起。玻璃画最早见于十五世纪意大利天主教圣像画。由于绘制技术难以掌握,到十八世纪欧洲已经不再流行。但在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的广州口岸,玻璃画却大行其道,甚至成为广州画匠外销画的重要画种。 而珐琅的金碧辉煌和雍容华贵,符合宫廷审美。所以常能见到宫廷广式家具上,紫檀的深沉上,常镶嵌色泽艳丽、对比强烈的珐琅、玻璃油画,显得粲然悦目。清宫的内务府造办处,除了“广木作”,还有“珐琅作”,这些都能看到“广作”匠人的影响力。 羊城晚报:在陶瓷品类中横向比较,很多人认为广彩比不上青花。但您认为广彩广珐琅具有改变中国陶瓷发展走向的高度,为什么? 郭学雷:这是确凿无疑的。现在很多人觉得广彩不如青花重要,那还是认识不够。珐琅这套系统最先在广东落地,发展到广彩,接着到宫廷珐琅,到景德镇粉彩系统,都是通过这条线发生,无论是艺术高度,还是它在整个脉络里起的作用,都很重要。它改变了中国陶瓷走向,改变了中国陶瓷釉胎装饰的风貌。清代以彩瓷为主,康熙之前就是青花和五彩,到了广彩这套体系出现以后,粉彩就大量流行,其实粉彩背后的推手就是广珐琅广彩。这个脉络你要观察不清楚,你就不知道它的位置在哪。其实广彩的影响力和地位应该有更高的一个评价。 其实广彩有非常厉害的地方,康末雍初尤其雍正初年的广彩花鸟,是中国陶瓷历史上水平最高的,但是国内基本上没有,基本在海外,像大英博物馆、大都会、法国集美、英国V&A博物馆,或是一些海外大拍上偶尔见到。这些花鸟画得极其生动,色彩极其艳丽,能体现出广彩的艺术性和材料的优势。的确要把视野放宽,放在海外去,你才能接触到核心的材料。 叁 传承创新 “广作”未来有何方向? 羊城晚报:以广彩为例,以前我们看到历史上曾有岭南画派与广彩的结合,现在的状况如何? 郭学雷:这种富有学养的结合创作很重要。像早期广珐琅广彩里有一些诗文,你能看到书法很漂亮。我印象很深的一件广珐琅里,蝴蝶画得不仅纤毛毕现、五彩斑斓,那几条触须和爪子,栩栩如生,现在很难再临摹出那种生命力。当时有很多书画家参与广珐琅广彩的创作。我觉得早期的广珐琅广彩艺人,功夫是非常了得的。只是越往后可能越在做减法。 陈文敏:其实岭南画派参与的广彩制作,我们一直在实践。广彩的非遗申报文本,从市级到省级到国家级都是我写的。将广彩300多年的传承脉搏、技艺特征、表现形态等做一个梳理,就能看出其中的传承与创新。 广彩主要有四个主要形态:第一,传统绘制。从明代开始,在青花上加三彩或五彩,俗称为斗彩。第二,定烧瓷绘制。在一口通商后陶瓷制造业繁荣,进口了法国的珐琅彩、德国的液态金水,丰富了中国陶瓷的颜料材料种类。第三,是积金彩瓷(也曾因一首《白沙行》被误传做“织金彩瓷”)。1784年美国刚刚崛起,也需要展示文化自信。欧洲人喜欢的是纹章瓷,而美国不一样,要求大金量,内容丰富,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第四,就是你提到的岭南画派参与的广彩制作。这在以前也叫“文人画瓷”,但概念较模糊。辛亥革命前,岭南画派“二高一陈”(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成立了广东博物商会,与广彩商人刘群兴一起,在广州办过瓷画厂。令广彩吸收了岭南画派技法如撞水撞粉等,为广彩发展输入新鲜血液。 2005年时,我也曾邀请过杨之光、陈永锵、陈金章等岭南画派艺术家,参与广彩联合创作,在陈家祠展出时,反响很好。其实我从1999年开始举办不定期书画诗词雅集,持续至今也有20年,合作了上万件广彩,融入了诗书画印的传统文化内涵,我认为这是一个可持续的状态。 当然我认为,不能说高端路线或大众化哪一个才最好。因为在广彩最出彩的时候,也是高中低档产品都有,有完整的系统,产业链才健康。非遗很重要的一点是活体传承,而不是把非遗的项目变成文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