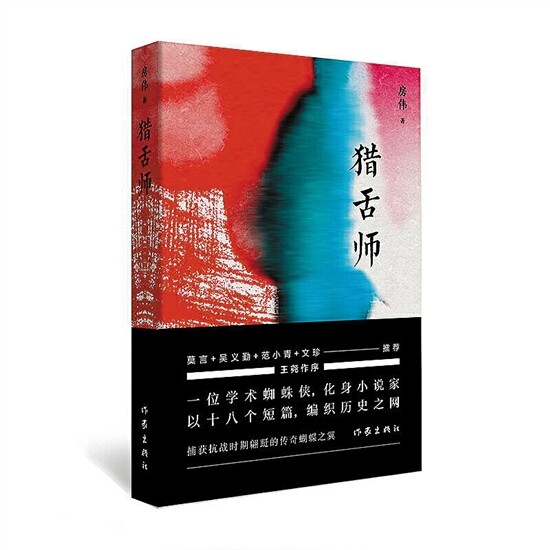
|
|
|
“历史”是一个丰富的文学资源库,神秘又暧昧,温情且残酷,以致对历史题材的探索成为每个时代的作家都不可回避的主题。从“对历史的叙述”到20世纪90年代“新历史小说”对历史资源的重新探索,可以看到作家们从追求历史最大程度的“真实”到以历史作为背景符号按自己的理念进行想象虚构的思路转变。然而,传统历史题材小说所追求的“真实”只是一种对大历史的整体性把握,已经省略了许多历史细节,甚至成为特定时代历史观念的直白呈现。而在“新历史小说”的写作中,历史开始无所谓真相,意义被重构甚至消解,致使出现一些流于对历史的戏说,止步于戏剧性与传奇性的作品。 房伟作为文学研究者,对文学历史意识的反思必定有不同于创作者本身的视角。因此在《猎舌师》这部小说集中,他以作家的身份试图对抗战历史题材进行细致的挖掘与另类书写。这部小说之所以能够使读者耳目一新,正是由于它以文学接近了历史褶皱里潜藏的“隐私”,并以诚恳的方式将它们呈现出来,形成了一种“刺痛”的震撼。 《幽灵军》中,长谷川中尉对虚云和尚说:“我们都是历史的隐私。谁也不会注意历史的隐私。不会在意川军,或你我的生死。我们的善与恶,也不会改变历史。隐私不能拿出来给别人看。战争不过在你我的心中……”历史有一种残酷的概括性。在当代人的抗战记忆中,改变历史方向的是那几次值得被载入史册的战役,是几场轰轰烈烈的起义,是几位横空出世的乱世英雄,以至于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些就是历史的全部。所以很大程度上,我们所谓总体的、主流的历史,也是一部“省略”的历史,而被省略的就是这些历史的隐私——由于无法改变历史的主流而不被注意的那些复杂的人性冲突。这部以抗战历史为主题的中短篇小说集,作家以悲悯情怀和严谨态度去挖掘被“省略”的历史,寄托现实关怀。 小说集《猎舌师》中的人物并不是随意捏造的,在小说集《后记》中房伟提到,“《中国野人》取材于北海道的中国劳工的原型,《幽灵军》取材于南京大屠杀后失踪的川军部队的故事。《肃魂》取材于肃托事件。《副领事》《起义》《花火》《猎舌师》《鬼子妮》等小说都有历史事件或人物的原型”。在史料搜集与挖掘的基础上,作家从这些真实的历史原型中触碰到了长久以来文学历史意识的盲点,即战争中个体生命的生存境遇与幽微心理。 小说集中刻画了多个与当时的大环境格格不入的人物形象。在《花火》一篇中,带着3万元军饷当了逃兵的参谋长,在逃跑中疑惧的模样仿佛《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他起先怀疑是什么兽物,但仔细看,又不像,分明是人的轮廓,但走路的姿势,有些像猿,佝偻着身体,异常灵活,有时低伏,有时雀跃。他愈发惊慌,猛地回头大喊:‘出来吧!如果要取我性命,尽管来吧!’”的确,房伟笔下的参谋长与鲁迅笔下的狂人,在某种程度上可谓是跨时代的“同病相怜”。同患有“被迫害妄想症”而“不正常”的狂人一样,参谋长“只想做个快乐的富家翁,好好活这一辈子”的愿望在整个民族浴血奋战的大背景下也“不正常”。但作者并未以谴责的立场来叙述参谋长幽微的心理变化,而是借这一人物来说明个体生命的内在矛盾与冲突本身就是一段历史最为真实的写照。作者将骁勇善战的参谋长与自私怯懦的逃兵这两种极端对立的角色融于一人,其实是在追问我们用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眼光粗暴地审视历史态度的合理性。这个形象的价值在于他表现出了战争背景中一个人像“人”而非政治符号的样子,虽然这个人物的命运不可避免地走向悲剧。除此之外,《起义》中希望带领队伍投靠共产党的国民党师长,在重病濒死时为了撑到起义的时机,警惕着周围,“像精明的老守财奴那样算计时间”;《鬼子妮》中从日本兵营中逃出的军医“山大爷”虽在中国娶妻生子本分生活,因为“不想杀人,也不想被杀”,但哪怕战争结束,他尴尬的异族身份与血腥的战争历史纠缠在一起,使他成为一个无根的人。 在房伟的写作语境里,“个人”不是无知无觉地被拍在河岸上蒸发的小浪花,而是具有个体生命力量的“游鱼”,虽然对于改变历史显得无足轻重,但他们鲜活且真实。 在众多历史题材小说中,“全景式”和“史诗式”的描写仿佛作为一种传承,到现在仍是很多作家无法解开的情结。但房伟则另辟蹊径,他开始以一种未曾亲历历史的身份严肃地回望历史。这种回望虽然秉持着一种尊重历史的态度,但他并没有使其拘泥于史实,而是试图以一种更加理性的态度,而非刻意丑化或神化的思维,将战争历史推入更高价值的思考中。 除了同一时代背景下两种文化的对话,小说集中还存在不同时空的并置。《回乡》描写了为了写出抗战历史的深度采访,解决编制问题的安心,回到故乡的红色堡垒村进行资料搜集。此篇小说采用了镶嵌式的叙述结构,在安心探访历史的过程中嵌入中学教员黄矜墨的日记内容指引安心与读者的真相探索,但最终现实生活与历史真相之间总有一条无法逾越的暧昧隔阂。除了《回乡》,《白光》《指南》《五三》等作品也通过历史尘埃与现实生活的并置,表达了不仅是当代人在回望和重塑抗战记忆,抗战记忆同样也在重塑当代人的现实生活的深刻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