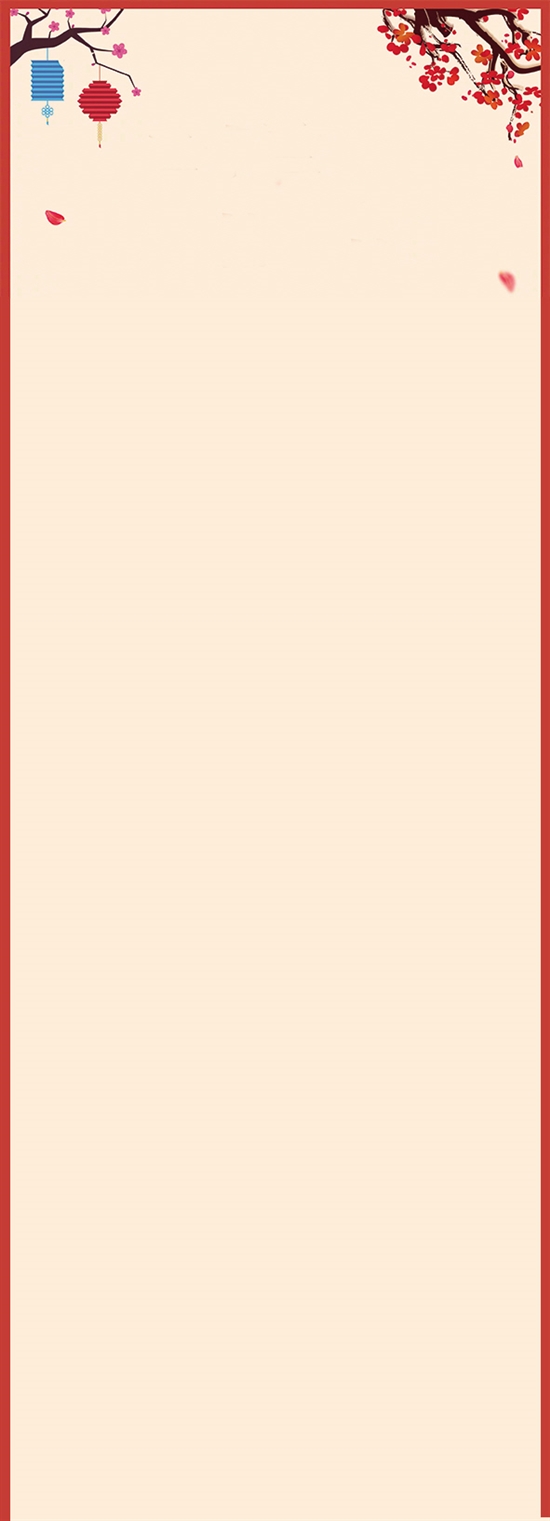
|
|
|
□谢新源 也就是一阵北风,白绒绒的雪紧跟着飘落下来。不大会儿,屋脊和麦苗儿上也为雪花所笼罩,田野和村庄银装素裹,一览无余。风雪中的村子鲜见有人出门,并因了雪景的衬托,在越发显得安宁的氛围中又平添了几分恬静。 一只急于觅食的喜鹊,孤零地站在高高的老枣树的枯枝儿上,四下张望,并不时“喳喳喳”地叫,叫出一派天地的沉寂和沉寂中的喜气。 冬,说到就到,仿佛就是一瞬间的事儿。 不过,这仅仅只是故乡初冬时节短暂的宁静景象,用不了多久,便会重新热闹起来。先是村东头焦爷家的豆腐店腾起一股股白烟,传出淡淡的卤水味;紧接着村西二小队也拉开了做粉条的架势,红薯粉碎机从早响到晚。晾晒场上,新出锅的粉条,被撑杆撑着,挂于铁丝拉线,一排排、一行行,在阳光的照射下散发出晶亮的光泽。尤其是,村北街谢老头家的香油坊、村南街三小队的豆油坊,一南一北、一大一小,几乎同时开张,于是,整个冬天我们这座坐落在豫西北平原一隅、千把口人的古而小的村落,便被时而浓烈、时而轻淡的阵阵油香包裹。每天,人们一大早出得门来,就像呼吸着早春二月的梨花香,心旷神怡,神清气爽,成就了一天的好心情。 气温一直在走低,雪花像是被风搅起的杨柳絮,在风中密密扎扎地漫舞。地上的雪亦越来越厚,一脚踏上去,能够听到它发出的“扑哧、扑哧”的响声,于沉静中显出别致的天籁般的韵味。油香也随着雪中的风飘向田野,飘到更为遥远的四邻八乡。邻村人家谁都知道我们村开着几间作坊,不用敲梆子转乡吆喝,大家伙到了该换油、换豆腐、换粉条的时候,自会拎着自家的芝麻、黄豆,拉着装满红薯的平板车,来到我们村,按照约定俗成的出品率,过秤、取油或豆腐粉条、走人。并且,被后来当作上等肥料的豆饼油渣、豆渣和红薯渣,如果不愿带走,还可作价抵钱,当场再买了油、豆腐和粉条,高高兴兴带回家去。 这样,我们村便一日热闹过一日,宛似赶庙会、早集一般,亲戚、工友、同学、远邻、男女老少,从东南西北汇聚而来。不同村不同俗,不同村亦语不同调,不变的是见面时那打招呼的热情、那开怀的畅笑、那紧紧相扯久久不愿松开的手。问候声、邀约声、说笑声此起彼伏,原本安静、甚至有些冷清的村庄,皆因了这几间作坊的存在,而释放出浓酽酽的乡梓乡情…… 雪下得再稠的时候,年关抵近。从入冬大多数时候藏在云后面的太阳,天天颇为识相地拨开云翳,探出头来,将久违的光芒洒在了厚厚的雪地上,天寒地冻中终于透出难得的暖意。家家户户开始就着有些儿刺眼的太阳购买年货,蒸馍馍、过油、包饺子、扫屋清院和贴对联。四间作坊越发显得忙碌,粉条、油、豆腐这些必备的年货更是抢手,粉条作坊门前甚至挤着满满当当的人。 他们开始了各自的加班。先是南街三队的豆油坊里,五六位壮汉,屋外哈气成冰,而屋里的他们则只穿着粗布裤头,边喊着高亢的号子,边抡起30斤重大铁锤,富有节奏地砸向一根粗硕的木楔子。正是汇聚到这根木楔上的千钧挤压力,将夹在两根屋梁般粗的豆饼愈挤愈紧,其中的油便被一滴滴给挤了出来。而北衔的谢老头则把推磨磨芝麻浆的儿子给换了下来,套上只小马驹,快马加鞭,拉着那盘小石磨,飞快地转动…… 村子上空油香弥漫,和着面香味,甚至蓝色炊烟里的柴火味;和着急促的切菜、剁肉、剔骨的刀声,翻滚的油锅所发出的咝咝声。这大概就是我们这帮少年伙伴期盼已久的年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