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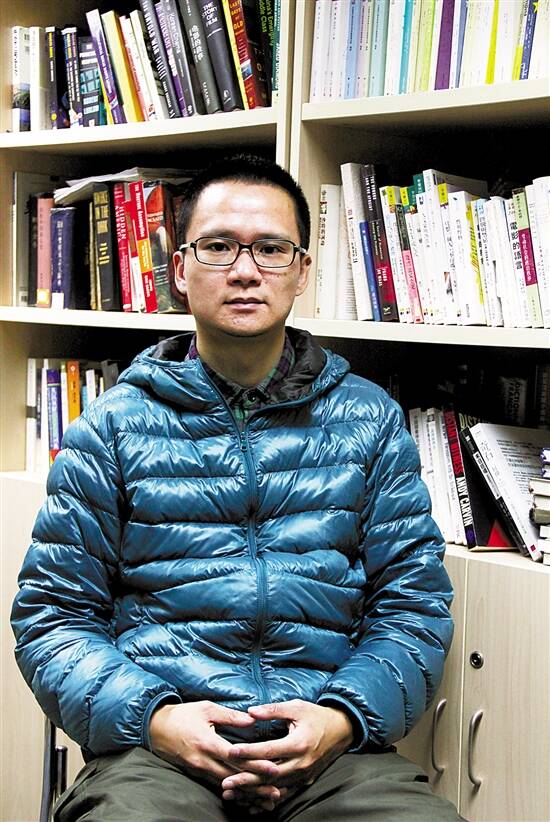
|
|
|
□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 古今中外都不乏瘟疫题材的文学作品,疫情当前,这类文学作品成为热门读物。《血疫》在豆瓣上评论过万,这种非虚构的写作手法更科学、更真实地呈现瘟疫本身,满足了当下的阅读需求。另一方面,一些经典小说如《鼠疫》也重新回到大众视野。 文学应该如何书写瘟疫?是用文学之眼洞穿瘟疫,张望瘟疫背后的社会与人性,还是用纪实的手法回归真实的瘟疫本身? 《血疫》编者张吉人: 病毒可以突变, 人类可以改变 为什么瘟疫图书这么“火”? 羊城晚报:自疫情爆发以来,与瘟疫、病毒或者疾病有关的小说、电影很多都火了,比如《鼠疫》《流感》,《血疫》也在豆瓣上火了,评论量过万,请问您是如何看待这一现象的? 张吉人:这种现象很正常,这跟人为什么要阅读有关,一方面我们会读一些古典、经典的东西,大家都公认这些东西我们必须要读。此外还有一些跟我们目前关心的东西有关的。这场疫情来了以后,大家很自然地去关注跟病毒、瘟疫、人与自然相关主题的书籍。这是读书市场很常见的现象。通过阅读这些书籍,一方面可以了解相关的知识,另一方面有调节情绪、调节心态的功能,这些功能在当下都是非常有效的。 羊城晚报:目前出版界里与瘟疫相关的文学作品多吗?市场情况大概是怎么样的? 张吉人:图书出版有一个时间周期,相对来说会延迟一些。我相信以后大家对病毒、公共卫生、医学、医护群体会有更多的关注,相关主题的图书也会变多。科普图书这几年,不管是引进还是原创,政府方面都在大力推动,而且有很多的政策,希望大家能出版更多更好的科普作品,可能因为这次疫情以后会更多一点。 羊城晚报:很多人都觉得《血疫》是一本很恐怖的书,您觉得呢? 张吉人:很多人觉得这本书第一章写病毒很可怕,但其实对我来讲,真正让我感到头皮发麻的是最后那句话:它还会回来的。这句话写在1994年,20年后,2014年,它回来了,而且是以一种更加惨烈更加凶猛的方式回来了,攻击范围更广。 《血疫》与《鼠疫》谁更好? 羊城晚报:您提到《血疫》写疫情很有特点,这个特点可以展开说一下吗? 张吉人:《血疫》是很典型的美国的非虚构写作手法,它处理的是科学问题,病毒跟人的关系,说得更大一点就是自然跟人的关系。但是它的写法跟一般的科普书是不一样的,里面有很多文学性的手法,有人物,有非常丰富的场景细节描写,故事的推动性很强,可读性、可看性很强,我个人觉得是科普写作里面最好看的一种。 羊城晚报:这种文学性的写法有没有虚构的成分呢? 张吉人:虚构的成分是没有的,非虚构的基本要求就是不能去虚构一个人物、一个事件,不能虚构故事的走向。当然里面有很多细节,尤其是对人物心理的描写,其实这些细节跟心理描写都是作者在对当事人的反复采访跟核对之后写上去的。 羊城晚报:说到虚构跟非虚构的话,现在特别火的《鼠疫》就是一本虚构小说,那如果将《血疫》与《鼠疫》放在一起对比,您觉得二者对瘟疫的表现有何异同? 张吉人:《鼠疫》这本书我很早很早之前读过,这本书给我的感觉就是,加缪写的瘟疫从整本书的角度来说只是一个背景,作者主要不是写瘟疫是什么或者背后的科学是什么,而是写瘟疫发生后,不同的人对瘟疫、对灾难的反应,我们通常把加缪归为存在主义,他的书有很深的哲学意味,加缪是把人放到瘟疫这种极端的状态下去呈现人性。 但是《血疫》中疫情病毒不是作为背景,而是作为非常重要的写作对象来写的,因为瘟疫背后有很多科学的东西,病毒到底是什么,微生物到底是什么,科学是如何认知它们的。 当然,这两本书也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比如在危机的面前,人的反应是什么样的,不同的是《血疫》既要写病毒本身,同时也要写人,两者需达到平衡。 人类需要做出什么改变? 羊城晚报:当下涌现出许多抗疫作品,您有关注吗?文学对疫情的呈现,或者延伸来说灾难文学的书写在您看来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张吉人:没有,我更多是看新闻报道,因为我们还在当下,还没有走出,我个人觉得需要看到更多事实,不需要太多观点。 当下也可以反思,但我觉得更多的是要走出来之后,在事后对事件有一个整体的认识,到底这个疫情是怎么发展的,有哪些关键的事实,有哪些关键的节点,当我们都认清之后,再去书写会更好,在疫情结束之后,可以在更完整的事实基础上去反思去书写。 羊城晚报:在您看来这次疫情对整体社会有何影响? 张吉人:大家对野生动物,对其他的物种包括对病毒、对整个自然界的看法可能都会发生变化吧,说穿了是因为病毒造成的大规模传染病不断纠正我们对自然原有的无知跟傲慢。另外,在极端的状态下,人与人的关系,人对自己的看法也会有变化,疫情当中我看到人的各种表现,恐惧、害怕、不信任、怀疑;也有很多很正面的,比如说医护人员的牺牲精神、专业精神,在极端状态下看到人性的方方面面。 为什么进入21世纪后这种新发病毒出现的频率,或者这种病毒的跨种族传播越来越多?这跟我们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息息相关的。人类的扩张,尤其是在非洲这边,我们侵入了更多的非洲的原始森林,导致我们跟野生动物、病毒圈的接触越来越多,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人类该做什么,既然病毒可以突变,人类也可以改变。这次疫情我们已经改变了很多,我们改变了很多生活习惯,比如自动隔离、学会了经常戴口罩,回家就洗手,面临新的情况,这是自然界要求我们必须做出改变。 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徐国荣: 灾难文学的书写原则 与瘟疫有关的名家名作 羊城晚报:历史上中国最早出现疫病大概是什么时候?当时采取的措施对当下有何借鉴? 徐国荣:我国历史上最早有文字记载的疫病流行是商朝时期,甲骨文中已有记载。历史记载中的大规模流行病很多,几乎每个朝代都有,明清时期达到高峰,大小规模的疫病几乎每年都有。大致说来,盛世时虽然也有流行疫病的发生,但一般朝廷控制得当,死亡人数较少,而战争年代与乱世中,流行瘟疫容易发生,而且往往惨绝人寰,死人无数。因为政府无力控制,经济条件也差,结果从小规模发展到大规模。 所以,从历史经验上看,及早控制,及早预防,举全国之力,团结一致,积极抗疫,结果往往较为理想。 羊城晚报:在您的阅读经验中,印象深刻的书写疾病或瘟疫的作品有哪些? 徐国荣:我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对于古代瘟疫书写的作品,印象最深的是三国时期曹丕、曹植兄弟对于建安22年那次全国性瘟疫书写。在那次瘟疫中,全国死亡人数很多,建安七子中的五位都未能幸免,曹丕在给朋友吴质的书信中谈到此事,表示非常伤心。曹植有《说疫气》一文,说到这次疫情,“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可见当时的惨状。这次瘟疫可能是伤寒病或肺鼠疫。 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多次瘟疫,每次战争或自然灾害之后往往伴随着瘟疫的流行。文学史上很多描写社会苦难的作品其实往往与瘟疫的流行有关。有些在文学史上著名的文学人物也与瘟疫相关。比如,苏轼两次居官杭州时,都遇到瘟疫,当时死了不少人,苏轼还因此向朝廷建议减税,积极抗疫赈灾,为百姓做了很多好事。而“初唐四杰”中的卢照邻便是死于当时的传染病——麻风病,他生前写过《释疾文》《五悲》等反映瘟疫的作品,但连当时的神医孙思邈也未能医治好他的病。 羊城晚报:在您看来,文学作品比如《鼠疫》对瘟疫的反映是否成功,对现实有何借鉴意义? 徐国荣:《鼠疫》是法国小说家阿尔贝·加缪的代表作,也是存在主义与荒诞哲学的经典小说。仅就《鼠疫》来说的话,运用的当然是一种表现手法。《鼠疫》本来就不是纪实文学,书中描写的鼠疫也不仅仅指代瘟疫本身。至于是否成功,要看从什么角度看,如果从艺术效果上看,还是非常成功的。但如果从社会影响上看,比如对现实的借鉴意义,更多时候恐怕只能再次引用黑格尔那句老生常谈的话:“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的教训,就是人类没有从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 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 羊城晚报:当下,涌现出大量抗疫的艺术作品,文学中抗疫诗歌最多,其次散文,小说较少,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徐国荣:因为从形式上来看,诗歌最好写,散文其次,小说最难(再次强调,仅仅是从形式上来看)。因为诗歌往往篇幅不长,又适合于“吟咏情性”,对于发抒情感与表达情绪比较简单而又快捷。散文在记述上有其文体的特长,而小说需要人物、情节,还需要典型的事件或人物形象,在目前抗疫尚未完全结束的情况下,也确实不适于过早出现。若干年后,一定会出现以此为原型的小说类作品。 羊城晚报:您觉得什么样的“抗疫”文艺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 徐国荣:忠实记录,真实记录,诚挚反思,深刻反思。 羊城晚报:文学对瘟疫的呈现,或者延伸来说灾难文学的书写,我们需要注意哪些原则? 徐国荣:不可美化灾难,不可擅自替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原谅”。目前还不是急于表达的时候,而是如何救灾抗疫,然后反思灾难是如何发生的,人们应当如何规范自己的行为。 对于灾难,作家除了记录之外,更要有悲悯情怀,应该对于他人与社会灾难感同身受。那些庆幸自己拒绝“九头鸟”的所谓“诗人”,当引以为耻。而所谓的感谢什么“冠状君”,其实是以社会灾难为对象,实有语言贿赂之嫌。 羊城晚报:都说人类的历史即是疾病的历史,瘟疫在给人来带来巨大创痛的同时,也参与了人类文明的进程,那么在您看来这次疫情会对整个社会乃至个体的精神世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徐国荣:这次疫情,反映了不少社会问题,特别是关于人与自然如何和谐相处的问题。其中尤为特殊的是人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关系。我们应该怎样善待野生动物,它们与人类自身究竟是什么关系;在重大的社会灾难面前,每个人应当担负什么样的社会角色,遵守什么样的社会规则,人性的光辉与丑陋往往都能在大是大非面前表现出来。知识分子更应该对此给予深刻的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