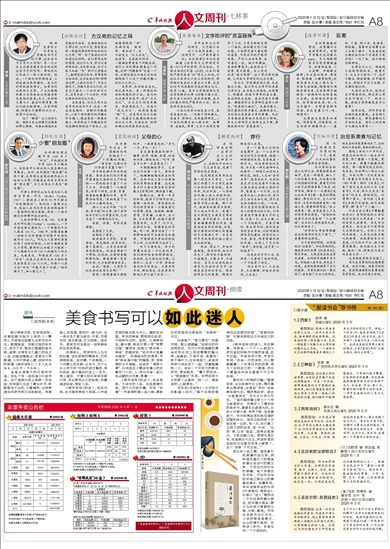|
|
|
黄维樑 香港学者、作家 多年来华文文学的研究,几乎被小说这个文类所垄断。小说研究中,以严歌苓最火红;本栏前曾引用古远清编著《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年鉴·2017》中的资料,作为佐证。月前出版的《年鉴·2018》,让我们看到严歌苓真是“热”得火上加油。对这位北美华文小说大家的研究,种种期刊发表的大量论文不算,光是2018年内地高校完成的硕士论文,就有16篇。复旦大学教授郜元宝近有吸睛的文章《好像不看小说,就不是人似的》,我改用其题,成为《好像不研究严歌苓的小说,就不是研究者似的》。 小说从近世兴起发皇以来,其受读者欢迎,一向胜于诗和散文。读者多、影响大,自然值得研究。二十世纪的理论如心理分析、叙事学、后殖民,等等,又为小说研究增开了门径,于是它渐渐变得一门独热,诗和散文则门庭冷落。小说研究者又喜欢跟风追星,乃有近年的严歌苓现象。严的小说和电影,我观看过一些。她才华横溢,是讲故事高手;我指出这个现象,毫无贬意。我心悲凉的是“趋炎附势”,这个学术界的偏颇,已导致文学研究的生态失衡。 古与今,中国都是诗之国,也是散文之国。就以华文文学中的香港文学而言,我书架上所存放,如胡菊人、陈耀南、岑逸飞等等的杂文集,各具特色与成就,显出作者才华横溢,都值得华文文学研究者深入研究,“发潜德之幽光”。先秦的散文,现代鲁迅的很多散文,就都是杂文。专栏杂文是香港文学的重镇,对众多香港读者有细水长流的大影响。华文文学研究应保持生态平衡,要避免批评的“贫富悬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