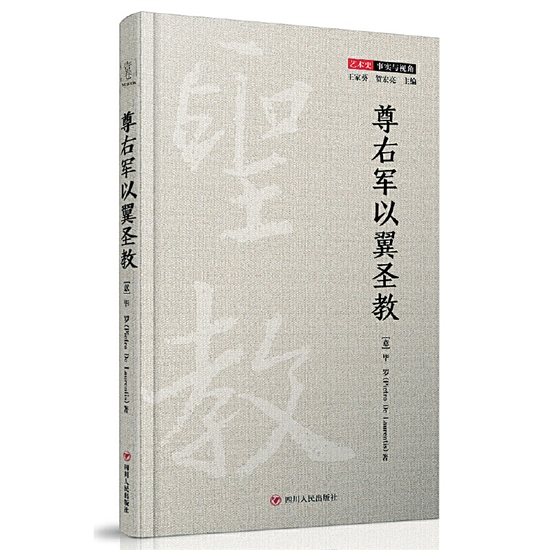
|
|
|
一个外国学者洞开一片学术新天地 上个世纪90年代末,触目都是一些诸如美学、文化之类的著作。就书法研究而言,也充斥着不少借西谈中、讨论书法义理的文章。当时的感觉是,凡是理论研讨,不引用西哲著述仿佛就不预流;而诸如文献考据之类的实证研究,则人迹罕至,多少让人唏嘘感叹。 但是没过多久,学风隐然发生改变,诚如李泽厚所言:“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近三十年,无疑是“学问家凸显”的时代。就书法领域而言,书法史之于书法美学、书法批评拥有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不过也应该看到,真正好的成果也不多。白谦慎教授从社会学角度对于傅山的叙述,张天弓先生援引西方语言学切入书法欣赏问题,祁小春教授浸润着东瀛风尚的王羲之研究,都获得了业内的好评。事实表明,多元的学术背景和独特的研究方法才是决定学问家是否超群出众的首要条件。 我的好朋友毕罗(Pietro De Laurentis)先生无疑是一位出众的“学问家”,不仅如此,他还具备作为一名“思想家”的潜质。阅读他《书法的书写过程与其序列性》,可知他对于西方语言学和符号学的熟悉程度。相对于国内书法研究者而言,毕罗身上所具有的西学修养无疑是让人羡慕的。但是毕罗认为,研究中国书法,西方学术背景不存在任何优势,他需要做的,是一头扎入中国古典的传统。我惊异于毕罗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努力学好汉语的同时,能对中国古典目录学、版本学涉猎到相当的深度并能写出极见功力的学术论文,这显然不是一般人所能梦见的。 新近出版的《尊右军以翼圣教》集中体现了毕罗近年研究中国书法所取得的成就和所达到的深度。在中国书法史上,成就最大而且广为人知的人非王羲之莫属,在传世的所有署名王羲之作品中,《集王圣教序》以篇幅宏大、来源复杂、艺术精湛而引人入胜。毕罗做了一项前人未曾做的工作,就是将《圣教序》中的1903个字形(单字755个)一一检证,察其字形,观其笔法,考稽来历,推阐微意,将《圣教序》中的单字与王羲之存世的作品建立了对应关系。 繁琐细致的考证工作往往会湮灭“思想家”的激情,但是对于“学问家”来说,却是发现和解决问题的法宝。另一方面,“学问家”的思考力也会在艰难的考证过程中得到激发。对于一个具备“思想家”潜质而且熟悉西学传统的毕罗来说尤其如此,当他面对一个陌生的领域时,迎难而上的结果是让他洞开一片学术的新天地。 王羲之是中国的达·芬奇? 毕罗深知,中国书法绝不仅仅是艺术,他对《集王圣教序》的研究,目的在于借此探讨中国中古时期顶峰阶段的初唐佛教与书法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集王圣教序》是佛教信仰、皇家支持和书法魅力三结合的产物,其中佛教宗师玄奘、唐王李世民和书圣王羲之成了支撑此一论题的“三足”。毕罗强调,“希望通过本书能够促进书法史研究,充分利用和接受历史、文化、宗教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营养,使得书法研究最终获得其应有的文化学地位。”毕罗充分地运用了敦煌文献资料,与流行的将佛教文献当成“知识精神的一般产物”不同的是,他将佛教文献的根本功能定位成“引导开悟”,在解释佛教徒的书写活动时,他特别强调精神的重要性,声称“中古中国的书写世界充满着极大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毕罗的研究也浸染着这样的精神。 围绕《集王圣教序》的实物和文本研究,毕罗充分运用了史源学、版本学、校勘学、目录学等传统文献学的方法,同时从文化学、社会学的角度将问题进行合乎逻辑的延展。他依据《圣教序》“当常现常之世,民仰德而知遵”中“世”和“民”的连用,得出“显然有意识地把他(李世民——笔者注)的名字留在《圣教序》之中”、“无疑是为了强调他本身对佛教的感情”的结论,这似乎超越了一般的逻辑推理,毋宁说是如有神助的“悟入”了。他通过历代著录和传世作品的统计,指出“当时怀仁所依据的王羲之作品往往比现存的几十件行书作品要多得多”、“《集王圣教序》中的1903个字只是当时所存王羲之行书字数的19%”,从方法的运用到结论的得出,刷新了常人的既有认知,可以看成是计量方法在书法研究中的创造性运用。 认识毕罗的朋友,都说他很接地气,已经非常中国化了。但是,这并不是说他同时也染上了自我设限的学科疆界意识。毕罗用他出色的研究提醒同道:“单独对原始资料的查阅方便对研究者并不会带来什么优势,对缺乏问题意识和批评精神的学者来说,原始资料本身也不会讲出什么。”面对怀仁《集王圣教序》近乎逼真地再现王羲之自然书写风貌,毕罗发问:“谁是《集王圣教序》的书者——王羲之还是怀仁?”这个发问无疑是相当具有启发性的,其背后隐而未发的是新历史主义基本观点:没有文本之外的世界,书法史隐藏在具体的文本之中。毕罗曾将王羲之比作西方的达·芬奇,将《兰亭序》比作《蒙娜丽莎》,这种中西融通的视野和不拘一格的想象力让他与中国的一般书法史研究学者区别开来。 毕罗经常来往于中国和意大利,非常注重实地考察和与中国学界的交往,这与我所知道的以往的汉学家不同。他的沉潜和专注已经让他的学术在中国大地上获得了立足之地,我们期待他有更好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