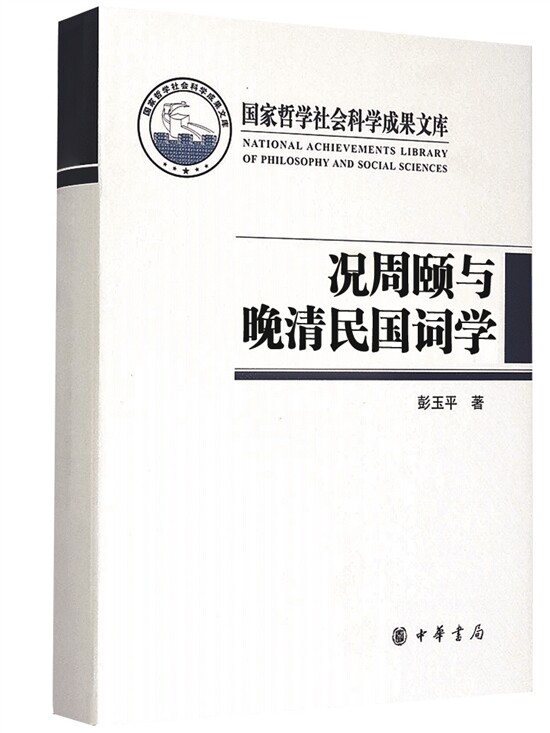
|
|
|
□彭玉平 我一开始想写的其实是一本叫做《况周颐词学研究》的书,但写着写着,竟然就变成现在的《况周颐与晚清民国词学》的书名了。这一转变的具体原因,实际上我也说不太清楚。但大致可说的是:况周颐词学其实承载着整个晚清民国词学的发展源流,他当然有专属于自己的词学思想,但他同时也是那个时代词学的聚合体。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读王国维是读作为词学个体的王国维;而读况周颐,则是在读一个时代。唐代诗人贯休说:“远浦深通海,孤峰冷倚天。”(《上冯使君山水障子》)形象一点说,王国维有点像清冷倚天的“孤峰”,而况周颐则有点像深广通海的“远浦”。 晚清民国词学:从陈廷焯、况周颐到王国维 我对况周颐发生兴趣其实在王国维之前。大学时候在随园的书店里,我就曾买过一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人间词话》《蕙风词话》合刊本,所以读王读况,几乎是同时进行的。但因为王国维的文字读来多有其来无端之感,未免抽象一些,我既然懵懂其间,搁置便也成了常态;而况周颐的文字则更为感性、更具诗情、更有光泽,自然也更容易吸引我的注意。读硕士时,我没写过有关王国维的文章,而写了一篇论况周颐的文章,大概是这一阅读感觉的继续了。看来纯粹跟着感觉走的学术,有时一样让人汗涔涔下的,因为感觉的欺骗性真是防不胜防。 我从学术角度对晚清民国词学的关注,粗粗算来,应该超过三十年了。最早细读的是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云韶集》《词则》《骚坛精选录》《白雨斋诗钞》《白雨斋词存》等,相关的研究成果大体收录在《中国分体文学学史·词学卷》(上、下)中,总有近20万字。陈廷焯从选本到词话的学术理路,从浙派到常派的词学宗尚变化轨迹等,皆清晰可辨。尤其是其在《白雨斋词话》中持“沉郁顿挫”之说衡诸词史,“以一驭万”,词学的格局固然不能说大,内在的逻辑却是相当周密的。王国维在早期的哲学研究与中年以后的文字音韵、历史地理研究之间,有数年时间沉潜词学,或考订词集,或辑佚词作,或编纂总集,或撰述词话,或考论清真,各有建树,而《人间词话》则在其中独领风骚。其以“境界”为核心建构境界说的多维体系,使得其词学带着鲜明的时代气息,也因此在整个20世纪迄今发生了巨大的社会与文化反响。 况周颐的名声大致在陈廷焯与王国维之间,但此处所谓“名声”的高下并不直接对应词学成就的高低。与在20世纪三十年代之前,王国维的词学备受冷落、黯然边缘的情形不同,况周颐从20世纪初开始便一直占据着词学主流的位置,在从祁隽藻、端木埰、王鹏运到朱祖谋这一脉的词学中,况周颐所得青睐特多,兼之博闻广识,天赋清才,使得其词学既渊源深厚,又自出手眼。故在词学界中,况周颐以兼擅填词与论词,而蔚成一时代词学之祭酒。即便王国维当年在词话中对朱祖谋、况周颐等晚近词人含沙射影,甚至偶尔失态,出言不逊,也丝毫不影响他们在当时词坛的领袖地位。而在三十年代之后,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便开始摆落诸种词话,一骑绝尘。 难以兼容的明流“重拙大”与暗流“松秀” 但实事求是地说,从对词体词学的专精而言,况周颐不仅探骊得珠,所得独多;而且不可替代,难以超越。这也是词学界一直高看况周颐的原因所在。但当下学界对况周颐的认知,在我看来,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其“词心词境”说自然别具理论光彩,而其“重拙大”说则如神龙出没,一直处于云障雾绕之中,难得一睹真面。而读《蕙风词话》者,困惑恐也不少。如视“重拙大”为词体本质与批评标准,何以词话之中,逸出之观念与评点如此之多,甚者与之矛盾对立者开卷可见?而在其晚年为刘承干代撰之《历代词人考略》中,何以“重拙大”的整体表述悄然消失?再回顾从20世纪初到二十年代中期,在诸种词话中,何以持续了二十多年的时间,而况周颐对“重拙大”说的阐释几乎没有变化,且一直散乱在词话各处,未能统归? 要厘清这些问题并不容易,但疑问总归是疑问,而疑问背后的精神考量其实不可回避,也不容忽略。如果翻检况周颐多种自述,我们大致可以知道,当王鹏运、朱祖谋等一帮晚清名臣发现了倚声天才况周颐,尤其是发现了况周颐的词学宗尚直追五代北宋之时,以我心忖度,他们是喜忧参半的。喜者不言而喻,忧者是如此天才如果任其别张一军,则在彼时彼刻,或难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当然,这还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如果将此等才华卓异之人引导到他们所信奉、追求的南宋“重拙大”一路中,则无疑平添一员健将,从此源流承续,前景可期。接下来就是语重心长、娓娓道来的劝说和教化。况周颐一开始的反应是迟钝的,或者说是抗拒的。但面对如王鹏运这样声望特出的老辈,他经过长达五年的犹豫、徘徊,最终还是表达了归附之心。 我不知道况周颐在做出这一决定时,内心究竟是清澈自如,还是混沌如初。我知道的是,此后况周颐果然在每一种词话的开头,都高悬“重拙大”的旗帜,以此表明自己的词学取向以及谱系所在。此在王鹏运,当可含笑九泉;而在朱祖谋等人,也是老怀堪慰。但他们终究还是小看了天赋的力量,源于本心的审美方向与对“重拙大”说的时时悖离,总在词话中顽强出现,而况周颐似乎无暇顾及两者之间的矛盾对立,一任其行。 我也是在反复的阅读中,发现了“重拙大”说固然是况周颐词学的一条明流,但如“松秀”等观念,则如一条暗流,虽静水深流,却也汩汩而出,蔚成江河。尤其是其大量持“松秀”观念以评骘词史之例,宛然别立一旗,另开一脉。而细检“松秀”之内涵,其与“重拙大”说并非双水并流,而是彼此碾压,难以兼容。我这才知道,对况周颐及其词话,实在是有重新认识的必要。这是我写这本书的最初一念,现在直言揭出。知我罪我,不遑计也。书中《况周颐与王国维:相通的审美范式》一章,也是与此呼应的。 我研究王国维词学,先做了一部《人间词话疏证》,然后再进入有规模的理论研究;我研究况周颐词学,也一直计划先做一部《蕙风词话疏证》,这项工作虽然至今尚未煞尾,但积累的材料已然可观。若论下笨功夫,倒真是无愧色的;但掩卷而思,我这才发现,其实只是向往之心而已,一直在艰难实践中,且成效甚微。但无论如何,这是努力的方向,有了方向,才有定力。而有方向和定力的学术,才是稍可放心的。 (本文节选自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彭玉平专著《况周颐与晚清民国词学》后记,原文49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