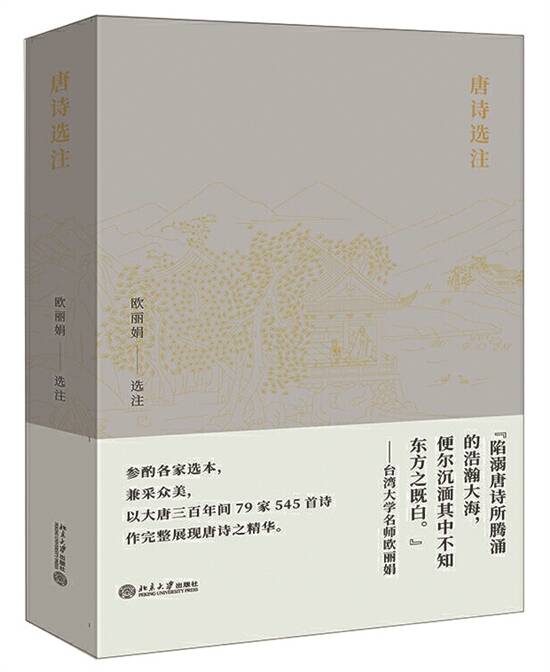
|
|
|
□欧丽娟[台湾] “偶然”里的“必然” 这部《唐诗选注》初版于上世纪的1995年,诞生自“偶然”。可在宇宙人生的运行里,“偶然”往往预示、引领甚至塑造命定的方向。倘若从“性格导致命运”的潜在逻辑来说,其实“偶然”也多半来自“必然”,是“必然”以意外的方式呈现的结果。 当时,初生之犊漫步于路上偶遇邀约,遂埋头读写,那是真正一笔一画的纸上作业。和学术论述的形态完全不同,书中展现的主体是一千多年前的诗人与诗篇本身,而不是我对他们的观察体悟;不是所有的材料彼此搭配、共同演绎出整体的起承转合,而是一个个作品自成体系,单独诉说某一永恒的瞬间。如此一来,岂非恰似昔日念大学时史学教授对《史记·孔子世家》之章法所做的比喻:一串珍珠! 每一粒珍珠都以诗人的灵魂为核心,凝结了某一瞬间的时空,展演了特定个体所专属的运行轨道,同时接受文字规范的严格限制,却也在艺术形式里高度升华,将每一份独特的情思、每一次不可复制的经历以最优美的面貌展现出来。抵消了尖锐刻薄,转化了龇牙咧嘴,成为纤敏的机锋和厚重的承担,通过抑扬顿挫的韵律耐人低吟寻味,通往人性的深层面。所谓“戴着脚镣跳舞”,这个比喻岂止是针对十四行诗,也不限于七言律诗,而适用于一切走到巅峰的真正文明。 唐诗当然是文明的最高体现之一。本书所收,都是千年以来历经严酷的检验淘洗而越发光亮的佳篇杰作,不只一篇篇深入诗人的心灵世界,也一页页推展诗国的版图,既可品悟字字句句所提炼的喜怒哀乐、所铺陈的人世风景,更能碰触到复杂深微的人性奥妙。确实,诗的力量在于感发,一种启动人心跳跃的力量,但那只是一个最好的起点,更有价值的,是在感动之后往更深、更远、更高之处进一步的认知,由心到脑,于思悟的层次上参透宇宙人生的奥秘。 唐诗的价值也正在这里。唯当时年少春衫薄,有好些诗篇的深不可测,得等待日后的磨炼才能洞晓。 杜甫的那份深情 当然,“偶然”在一开始时便已经蕴含着“必然”。选注的过程必须取舍,幸而此一取舍基本都建立于长期以来的共识上,大致无虑,只有一首诗是在几番挣扎犹豫之下,仍然以自己的主观价值放进书里,那是杜甫的《病马》。我衷心承认,它在杜甫的众多篇什里确实并不特别出色,甚至算得上平庸,却总不能断然割舍,因为第一次读到此篇时的心情始终鲜明,正是杜甫所谓的“感动一沉吟”。 那一匹忠诚的、沉默的病马,毫无所求,随着落难的杜甫艰辛地奔走于崎岖的路途上,与主人相濡以沫,杜甫感之、念之而形诸笔墨,岂非同样出自由衷的真情?无一声沦落之叹,无一丝愤懑之气,只有满心的感激与疼惜,而对象是一匹平凡的马。那不只是慈悲,更是谦卑,比起白居易的“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更厚实,较诸李白的“借问此何时,春风语流莺”还温暖。究其实,它分担了杜甫的苦难,在流离动荡中不离不弃,充分体现出康拉德·劳伦兹所说的“默默表示的深情”,而深深体味到这份深情的杜甫,又以先秦君子田子方的仁者情操,将一个笛卡儿所谓的“活动的机器”还原为天地所钟的美好灵魂,这是真正伟大的人道精神。如此的至善,诚殊胜于艺术的美,始为庄子所谓“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大美。 在对文明的评价里,我总认为“善”要比“真”与“美”更高阶,更前提,至少会让真与美更有正面的力量,所以我还是收录了这首诗。倘若因此而触发更多的人善待世间万物,大雅君子必能谅察区区之举。 面对书中所选的艺术杰作,评注者的工作有如烧制一砖一瓦,铺桥造路,其实承接了古今许多专家的心血,绝非单凭个人之力所能完成。值此简体版面世之际,必须感谢偶然的机缘与前人的资源,还有北大出版社尤其是刘方主任、吴敏女士所给予的协助。而即使路桥底定,但究竟会通往何处风光,依然存乎一己心志之所向,那才是“偶然”成为“必然”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