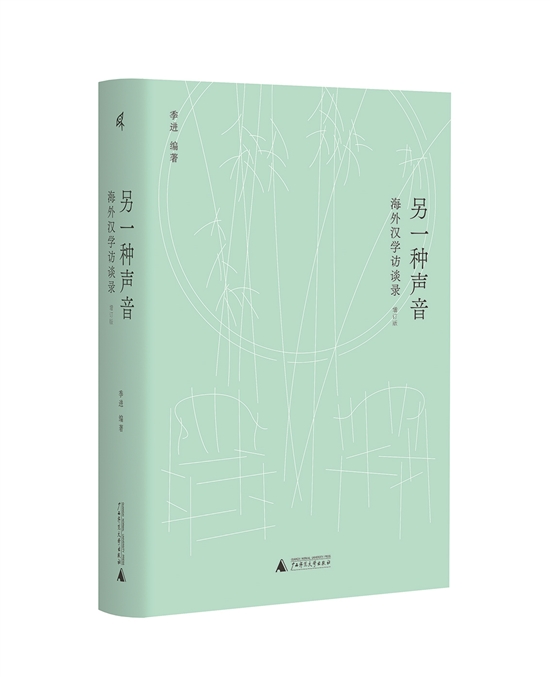
|
|
|
□乐黛云 季进在《另一种声音:海外汉学访谈录》一书中的访谈对象,已不限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还扩展到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在讨论中国文学海外传播过程中,包括宇文所安、阿瑟·韦利等汉学家,他们跨文化、跨语际的立场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访谈为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鲜活材料。 目前关于海外汉学的访谈著作并不少见,但在我看来,都不像季进的这本访谈,能如此既概观全局,又深入核心;既通透历史,又执着现状;既有理论深度,又是朋友间闲话家常,娓娓而谈,使访谈内容于不知不觉间,渗入读者心田,臻于润物细无声的妙境。关键还在于访谈者季进对海外汉学有着深厚的了解,对孕育汉学的西方理论也有较多的积累;又与这些汉学名家有较深的交谊和较长的交往,能在谈笑间摒除一般难以避免的隔阂、俗套和遮掩,直击心灵深处和事件核心;加以详密的准备,颇有技巧地将谈话循循诱导,使被访谈者沿着访谈者预设的思路,步步深入,并得到充分发挥。正因为如此,我欲罢不能地读完了《另一种声音:海外汉学访谈录》,颇得欣然忘食的喜悦,并有多处共鸣。 我一直关注如何对待西方理论问题,特别关注成长于西方文化语境的学者如何对待这一问题,因为这毕竟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比较文学研究不能不面对的一道难关。使我长期困扰的问题是:西方理论层出不穷,变化多端,真要完全掌握,直到精通拉丁文、希腊文,才能拿来应用吗?西方理论诸家并存,各有招式,真要进一家之门,沿一家之路,才能修成正果吗?西方理论各家自有一套概念系统,如果打乱这一既成系统,只取所需,会变得牛头不对马嘴吗?取其全套概念系统,用于中国文学实践,又是否会使中国理论有失语之虞?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这一在美国研究、品评、传播中国现代文学的“三家轴心”面对这一难关是怎样迈越的呢?他们的论述对我启发颇多。 夏志清一再强调要有自己的理论积累,他坚持“如果没有相当的积累,反而会被理论牵着鼻子走”。他说:“只要是优秀的批评家,我都学,才不管你什么派呢。”他认为不仅要看批评家的东西,还要看他所批评的作家。这个理论好不好,不仅一定要看他的原文和他批评的对象,还要看他走的路,他怎么会这么评论。 李欧梵则进一步指出:“现在流行的是先看理论,几乎每一本书一开始就演出一套理论出来,如果你没有一个理论来开始的话,你这本书就好像是很传统、很落后的东西。”他抱怨说,“现在我们看得太多的研究都是建立在一种莫名其妙的理论基础上,用了一大堆新概念、新名词,可是却没有新材料、新结论”。他的方法与此不同,他是先找出一些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然后参照脑子中储存的各种理论,得出自己的结论。在这个过程中,他提倡“将眼光放远,不再执着于批评和理论所暗含的道德优越性和知识(政治)的权威感,而专注于批评和理论所促动的复杂的理性和感性脉络,以及随之而来的傲慢与偏见”。他的思考对于反思一个世纪以来的理论和批评是十分有益的。 王德威则尖锐批评了某些海外学者追随西方的当红理论,并迅速转嫁到中国领域,以至于“理论干预”成了“理论买办”的现象。他认为对理论的关注,首先是为了磨炼批评的工具,以便更深入地探讨学术问题及其用心。任何理论和方法,其合法性应该建立在其是否能增进我们对某一文学现象的了解之上。 读完这些海外汉学访谈,收获当然远不止于此。其他诸如有关人文主义与知识分子边缘化的讨论,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抒情与史诗传统延伸为话语模式、情感功能和社会政治想象来研究,区分“再现”和“代表”的不同,指出“不能因为我的任务是再现中国,那我就真的代表中国”,等等,这些都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也都给我以深深的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