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王铭铭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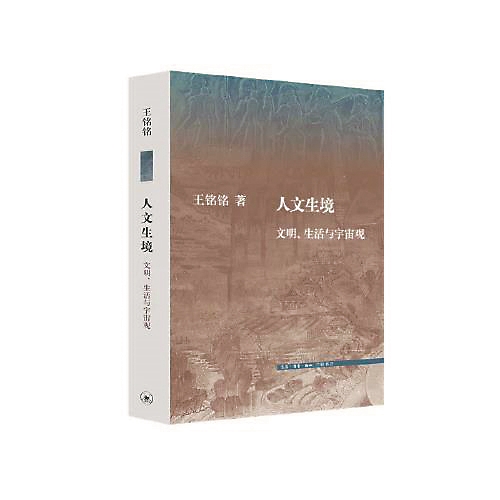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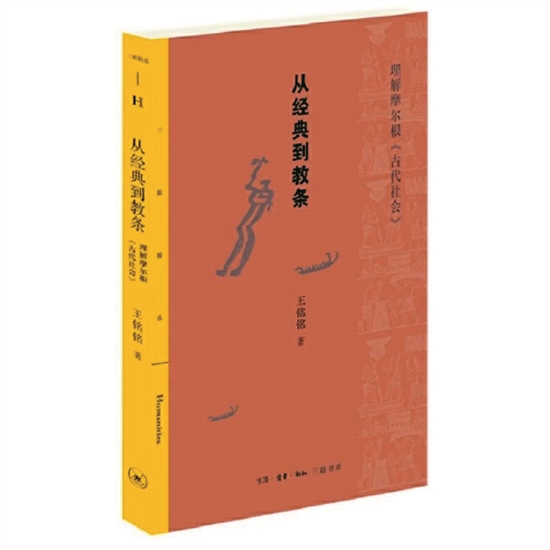
|
|
|

|
|
|

|
|
泉州开元寺 |
文/羊城晚报记者 吴小攀 近些年来,人类学家、北京大学教授王铭铭在进行人类学研究并推进其中国化的同时,也积极开展相关普及工作,尤其是有关中国东南、西南及欧洲乡村研究,引起学界关注。他同时也关注文明与广义人文的关系,撰写大量论著,最近出版了《人文生境》一书。近日,王铭铭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因缘巧合走上人类学研究道路 羊城晚报:您是怎么走上人类学研究道路的? 王铭铭:我少年时并没有接触过人类学,是进了大学后才了解的,走上人类学研究的道路,是因为有大学老师的引导。 羊城晚报:20世纪80年代初正是全民经商最热的时候,当时为什么您会选择这个专业? 王铭铭:我读大学时,“下海”的确是热潮,不少中小学同学经商去了,有的成了当时说的“万元户”(有钱人)。我考上大学,选了考古专业,我的家人和乡亲并不是很理解。说实话,我选择读考古,原因也不“单纯”,我只是了解到这个专业能提供一整年的田野实习条件。那时我急切地想着去老家以外的地方走走看看,而考古专业显然满足了这个要求。 我在厦门大学读本科之初,它还没有人类学系,我们系是在我大学三年级时才创办的。我本来蛮喜欢考古学专业,甚至想致力于商周考古研究。大学三年级时,老师们(他们多数是林惠祥先生的弟子)创办了人类学系。我们整个班级被转到这个新建的系里,我也就成了其第一届本科生。在读考古学时也接触到人类学,通过林惠祥先生的旧著和李亦园先生等的著作,以及来华讲学的“老外”的讲座,初步对它有所了解,也产生了兴趣。 我后来到英国伦敦大学念博士,他们教的人类学是社会人类学,与社会学比较接近,没有考古这个分支领域。去英国以前,我已经接触到20世纪前期留英人类学博士、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著作,深受其吸引。我是在老先生留学英伦50年后去伦敦大学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的。人类学有某种“好古幽思”,对现代性有深刻反思,这很吸引我。这恐怕与我个人成长经历也有关。我出生在泉州这座“遗产之城”,这座城里,即使是在“文革”期间,人们的行为依然“守旧”,习俗古朴。矛盾的是,它在古代却有过相当长的“海外交通史”。我觉得人类学有助于我在历史中审视,激发新思想。 羊城晚报:作为过来人,您认为兴趣、专业和职业三者如何取舍、平衡? 王铭铭:一个人的兴趣假如就是他的专业和职业,那他就是一个最幸福的人了。不过我们往往不是“最幸福的人”,因而需要在三者中取舍、平衡。这从一个反面说明,唯有认识到“最幸福的人”是不需要取舍、平衡的,我们才能做好取舍、平衡,在不如意(也就是三者不能达成平衡)之时,理解处境的由来,找到适应它的办法。 摆脱西方视角还有待努力 羊城晚报:如果要向普罗大众介绍什么是人类学,您会怎样介绍? 王铭铭:我很喜欢一些科普作品,它们往往出自于大师之手,深入浅出地把一门学科的对象、目标、方法、思想脉络、现状娓娓道来。我也努力过,比如,写过《人类学是什么?》,但我的努力好像并不成功,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现在对所谓“普罗大众”(其实他们多数是年轻的读者)有影响的,好像是别的东西了。特别是能适应年轻人口味的东西可能比较有影响,而我正在走向“老龄”。我深知在这种状况下,我们特别需要以科普作品如实介绍人类学,纠正误解,但我感到难度越来越大。 羊城晚报:人类学和历史学有何异同? 王铭铭:二者关系很密切,差异也蛮大。人类学曾经是人类文明史,是比历史学更宏观的历史学,后来变成以田野工作为中心的研究,出现了“反历史”潮流,但四五十年来,历史重新成为这门学科的主要内容之一,它与历史学关系重新密切起来。 人类学与历史学一样,都深深为“过去”所魅惑,人类学所谓“文化”“社会表象”,与“历史”一样,都是“过去”的产物。二者的差异点也有很多,比如,人类学家更信任口述和观察,历史学家更信任文字;人类学家的“历史”更像是“现在中的过去”,而不是历史学的“过去中的过去”。 羊城晚报:作为个体的人和整体的人来说,人类学和哪一个关系大一些? 王铭铭:一般说来,人类学与整体的人关系更大。但也不是所有人类学家都是整体主义者。在人类学历史上,存在过一大批“个体主义者”,他们有的以个体人的心理学为方法,有的以个人解放为追求。我自己则努力打破个体/整体的二元对立,试图说明个体是“含有”整体的。在《人生史与人类学》一书里,我阐述了这个观点。 羊城晚报:作为一门源自西方的学科,中国当代人类学研究“中国化”的程度如何? 王铭铭:一方面,这有待更多人关注,另一方面,讨论这种“化”的人往往只是在喊口号,其话语的内容在本质上并不是中国的,甚至往往是比西方更西方的东西。我觉得这很遗憾。 羊城晚报: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摆脱了西方视角? 王铭铭:这有待努力。 羊城晚报:当代中国人类学研究在世界人类学研究中处于什么样的水平? 王铭铭:中国的社会人类学曾出现过对世界学术有贡献的杰出学者,比如,大家比较了解的费孝通、林耀华、李安宅、瞿同祖、田汝康等。现在学科整体还有差距需要缩短。 羊城晚报:还有哪些方面的差距? 王铭铭:差距有许多方面,比如:(1)我们尚未形成自己的学统,因而讨论问题、处理经验和理论,都常常流于模仿西学的表面;(2)我们的大学人类学教学系统性不足、随意性有余,培养的人只好靠他们的天分成才,偶然性极大;(3)我们的区域研究视野有待扩展,纵深有待深挖,现在我们国力强了,人到处走,表面上有了某种“世界活动”,但“身游有余、心游不足”,思想上的收效甚微。 闽南已构成一个“学术区” 羊城晚报:关于闽南的人类学研究,除了闽南是您的故乡之外,从学术的角度来看它还有哪些吸引您的地方? 王铭铭:一百多年来,在与人类学相关的领域里,有关闽南的研究学术积累丰厚,而当下,这个区域也广受关注,有大批学者到这个区域从事研究。在我看来,闽南已构成一个“学术区”。作为一个“学术区”,它有自己的特殊问题意识。过去有不少学者在这里研究区域社会经济史,成就很高,他们关于“小资本主义”和“乡族主义”、礼仪与风俗、家族与信仰等等的研究很有启发。我对“民间信仰”比较关注。从学术角度看,我觉得闽南“民间信仰”里蕴含一些有待挖掘的“智慧”,这些“智慧”触及到我称之为“人文生境”的边界,关涉到人、物、神三者构成的“广义社会”,而这种“社会”,则又触及到哲学上的“内在”与“超越”的关系问题,很值得作为重点来研究和思考。 羊城晚报:闽南在您的学术研究谱系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王铭铭:我的经验研究开始于闽南(也兼及台湾的汉人乡村),接着,我有几年在华北乡村与域外徘徊,近20多年来,我则主要在西南区域从事学术活动。 闽南学术区是我经验研究的起始地。这些年我得空便要回到闽南去,曾出于机缘巧合带着学生在泉州安溪、鲤城、惠安做过几项研究,也组织过闽南研究读书会,情况在《茶·街·庙》这本文集里都有记载。两三年来,我回闽南的机会更多了,但我分心做了许多理论研究工作,做经验研究的时间和精力受到了越来越大的限制,只好随缘。现在有两个新一届的博士生在闽南做研究,都在研究“民间信仰”。他们如果能做好研究,写出有气象的作品,那我会很高兴。 做学问习惯于“跟着感觉走” 羊城晚报:老一辈学者往往有“学术救国”的理想,您这么多年从事人类学研究,觉得人类学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王铭铭:现在的人们更爱谈的是“把自己作为方法”,这意味着要把个人当作世界的尺度。我们生活在一个“后激情年代”,适时的“生存性智慧”恐怕是拒绝所有魅惑,沉浸于自己的“肉身日常”中,那样比较舒适而安全。也许是因为我并不是在这个时代长大的人,所以我还是长期受某种东西所魅惑,而魅惑也给了我某种“激情”。这股“激情”是来自“学术救国”吗?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我暗自觉得人类学意味着很多,对我们这个国家与文明意味着很多。若是我理解得对,那么,人类学的目标是为自己的文明跨出自己的文明、为自己的时代跨出自己的时代,“跨”既是方法,也是目标本身,但它并不是什么玄妙的东西,但要真的做到“跨”却不见得容易。 羊城晚报:您坚持这么多年的人类学研究的动力是什么? 王铭铭:是什么动力使我坚持做人类学而没有“绝望”?恐怕是这门学问的“魅惑力”吧。没错,它是近代西学,但我相信它有古代的苗子,我们的古代也有它的苗子,所以,我不觉得它等同于西学,我觉得它是“我”的一部分。 羊城晚报:有没有为自己树立一个高远的目标? 王铭铭:我不习惯为自己树立一个高远的目标,而习惯于“跟着感觉走”。从某个角度看,我做的人类学也不见得符合这门学科的严格定义(往往是狭义的),我只是在借它的名义来“做学问”。 羊城晚报:有没有设定放下人类学的一天? 王铭铭:我会放下它吗?“放下”这个词很值得玩味,你的意思估计是“不再牵挂它”?如果是这样,那我必须说,我暂时还依旧“牵挂”它。未来是否会“放下”?我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