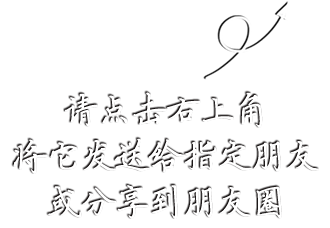陈一峰 《唯有牡丹真国色》水墨纸本
□伍世昭 王先岳 伍世文
二
历经多年的探索实践,陈一峰从笔墨到造型,再到意境的传达,已形成了一种可辨认的独特风格,以至于在鉴赏过程中,人们很容易就能从一大堆画作中指认其画。其兼擅油画、写生画、水墨大写意花鸟画,尤工水墨大写意人物画。但无论从画史还是美学逻辑的角度论,大写意人物画都堪称中国画领域难度系数最高的一科。以至于当下中国画坛,鲜有跋涉且痴迷于此道而如陈一峰者。偶有涉足者,或巧于重彩设色而拙于墨分五色,或学前人皮毛而气困于雕琢,或求收放平衡而势落于局促,或敏于形式翻新而轻于意境营构,不一而足。
陈一峰的大写意人物画与中国传统、当代和西方现代绘画都存在着“秘响旁通”的微妙联系,从这种相互联系中,我们或能发现某些重要信息。
陈一峰认为中国写意花鸟有大家,唯人物写意则鲜有高人。其常书一对联云:“绝顶人来少,高松鹤不群。”回望数千年画史,他发现了两个“大写意”大师:一个是五代的石恪,一个是南宋的梁楷。石恪之《二祖调心图》等画作“简纵狂逸”“不守绳墨”,开启了减笔人物画的先河;梁楷之《泼墨仙人图》诸作“逸笔草草”“气韵生动”,则进一步拓展了水墨写意的表现手法,从而成为水墨大写意人物画发展的里程碑。石恪和梁楷作为中国大写意人物画的源头,陈一峰对此当然了然于心。不过,梁楷由工整的院体画家转而为大写意减笔人物画家,似与他有相同的经历,故而其对梁楷有“前无古人”之慨。陈一峰指出,梁楷之后再无大家,明清之际虽有吴伟、张路、徐渭、黄慎、任伯年诸家,但已是强弩之末,“缺乏恢宏气象”。
二十世纪以降,由于写实主义、中西融合绘画取径的规制,人物画整体上进一步疏离了大写意的艺术精神。尽管如此,陈一峰还是勾勒出了20世纪下半叶以来大写意人物画的大致线索,并提及了几个“孤独”的名字:周思聪、石鲁、李世南等。从陈一峰的评价与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陈一峰画风所带来的启示与影响:他们对形意转换、夸张变形的探索;他们为“自由”“写意”提供的参照;特别是他们的画作所呈示的那种“放笔直写,解衣磅礴”的精神、生命原始的冲动以及“心象”的传达等等,都在陈一峰的大写意人物画中留下了程度不同的印记。所以他说:“站在他们的画面前,我们不会太注意画面许多技术性的问题,更多的是思考和感悟,更多的是感情的交流和共鸣。”
陈一峰在肯定与否定两种语气中对自古以来的大写意人物画家作出了自己的评价。但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他们的影响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陈一峰或是借鉴经验继承超越,或是吸取教训绕道而行,看来都是必不可少的。
陈一峰对西方绘画特别是对西方近现代以来的后印象派、野兽派和表现主义,有着相当程度的了解,他自己就曾多次在谈话中提及。当然作为水墨大写意的传承者,陈一峰关注西方近代绘画是应当的,事实上他刚刚涉足大写意人物画时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在我们看来,陈一峰受到西方近代绘画的影响,似可总起来考虑,即无论是后印象派、野兽派还是表现主义,它们产生的潜在影响或者说给陈一峰以灵感的潜在启示大致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即粗犷的笔触,富有意味的色块,强烈而单纯的色彩,形象的夸张、变形与简约,以及灌注于画中的强烈主观情感(感觉)。因为这几乎是上述几个派别的画家所共有的——正因为强烈的主观情感(感觉)的灌注,才使得他们的绘画具有迥异于传统的笔触、色块和形象,比如塞尚的《三浴女》、梵高的《向日葵》、高更的《玛利亚》、马蒂斯的《舞蹈》等等。陈一峰的绘画同样如此,“意境乃心境使然”,主体性情的勃发和主观情感的燃烧才造就了他那非同凡响的大写意的笔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这种心灵感应,才使他乐意从西方现代绘画中汲取某些养分。
三
在博采古今中西绘画长处的过程中,陈一峰逐渐形成独特的“大写意”之观念,而对其观念的理解与把握,则是阐释其画风特征与艺术精神的一把钥匙。
依一峰之论,写意即是“放笔直写”,表现在笔墨上首先是书法的引入。换言之,即中国画笔墨关于“以书入画”原理的实践与运用。这是阐明陈一峰大写意画风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视角。他之所以将大写意笔墨建构于书法的基础之上,是因为他勘破了一个“奥秘”:中国书法作为中国画笔墨的参照系,不但塑造了中国画在世界艺术之林中的独特性与文化品位,而且建构了中国画笔墨的方法论体系与艺道合一的美学理想。王先岳尝论陈一峰的笔墨“兼有草书的飞动之势和篆隶的浑圆厚重”,尤为凸显了前者,“以书入画”首重线条的运用,是其洒脱不羁自然流露的“本性”使然。例如,在《东坡诗意》《李白醉酒》等画作中,充满草情隶意的书法性线条即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其次,是勾勒、点厾、皴擦等技法的“交融并用”:勾勒一般是用线条勾描出物象的大体轮廓;点厾是用画笔在画纸上随意点染,对画作局部或细节加以修补;皴擦的要点则是笔锋水墨含量少,多横向或逆向着笔,画面蓬松毛糙、富有质感。陈一峰这三种笔法的运用均相当自如,且变化多端。就其渊源论,这些笔墨方式多源自山水、花鸟,其对人物画的影响与启发,给陈一峰的大写意带来了更为深刻、磅礴的表现力与笔墨方式突破的可能性。其笔下的线条勾勒,充分发挥了书法入画的独特表现力,同时结合人物形象的体貌特征、精神气质而应物宛转、随态运奇。而点厾、皴擦作为勾勒的辅助性笔墨,一方面丰富了其画面的笔墨形式,并形成点、线、面相结合的笔墨结构;另一方面也是画家为抒情写意而知权达变、随态运奇的需要。
第三,是团块性笔墨方式的强调与洇湿法的运用。方土所言“多变的块面”,即指其笔墨的团块性结构。如《张旭酒后狂书图》《独钓寒江》《论道图》等画作,其团块性笔墨方式的突出运用,使物象造型显得厚重苍茫,雄浑大气,富有雕塑般的力量和质感。这种笔墨方式,虽然不无西画影响的痕迹,但画家已然通过书法意识的融入,将西画那种单纯追求立体感的团块结构,转化为中国画特有的写意趣味。从某种意义说,团块性笔墨正是陈一峰大写意人物画凸显物象精神之“大”——即“大象无形”美学的独特方式!与此相关的是洇湿法的运用。水墨的扩散渗透,一方面成为笔墨团块结构形成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使得画面充满浩荡无边的沛然元气。但水晕墨章的笔墨方式极难把控,要做到恰到好处,则必须善于处理水墨的渗透问题,以发挥其与宣纸相融互渗的独特效果与审美表现力。
第四,是以夸张变形的笔墨凸显人物形象的体貌特征与精神气质。“大写意”,其表征于视觉层面,即在于其物象造型的“离形得似”“不似之似”,也正是老子“大象无形”之谓!而征之于画面,则画家往往以此打破人物身体结构的比例关系,从而给观者以迥出意表之感。其笔下人物的面部结构,有时连基本的结构关系也完全省略,而徒留头部的空线勾勒或团块状笔墨,比如《大汉雄风》等。其笔下人物的脚板,往往显得特别长大,而烘托人物形象的酒壶所处位置与大小也多半超离了常态——画家在创作一些乡土题材人物画时,这种处理方式几乎无处不在,比比皆是,从而形成了一种独一无二的“陈家样”。更为奇特的是,其大写意创作时或逸出常轨,打破人物、花鸟、山水之间的界限,使得三种完全不同类型的物象相互融汇,似人,似鸟,似山,而又非人,非鸟,非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