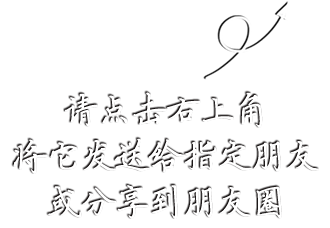□付炜
远远地,山的轮廓渐渐显露。连绵的一条墨线,在夜晚不断拓印着,那就是七娘山。
几年前,诗人黄灿然村居在靠海的洞背村,后来又搬到了这座七娘山下的村庄。我们抵达时天色完全漆黑,走下车立刻感受到一股早春的凉意袭满全身。村里很安静,几乎什么都看不清,只闻到一种莫名的植物散发着沁人的气息。偶尔从树丛里闪出两只野猫,也只是好奇看着我们,然后保持礼貌的沉默。
乡村的夜非常简洁,在这里你能想象有一种沉着、明晰的诗歌是如何写出的,因为万事万物一草一木都像是滤网,过滤掉人世的不堪与喧闹。我来过几次,每次走在通往黄老师的那条小路上,我的头脑里都会想起彼得·汉德克,他在巴黎的屋子后面也有一条小路,他常在那里思考、踱步,并称之为“永恒的小径”。
汉德克的那种生活,某种意义上跟黄灿然的生活非常类似,平静、简单、朴素,除了一切必要的,其他都不必要,而那些必要的也都是围绕着写作而展开,或者说为了写作而服务。二十多年前,黄灿然有本文集,名叫《必要的角度》,他在里面诚恳、认真地谈论了一些外国诗人。他非常认同布罗茨基对于诗人责任的认定,那就是写好诗。这么多年,他也一直用自己的写作去践行着这一点。
他的写作,从香港到洞背,再到七娘山下,一路走来,如果从外部来看,他从国际都市到一隅的村庄,似乎他的世界在日渐收窄,但他自己却不以为然。他觉得一个诗人不必去看那么多的世界,附近几公里地方、每天散步途经的路途,就已经写不完,用不尽。他年轻时多病,在香港琳琅炫目的街头,看那些巴士、招牌、茶餐厅里的侍应生,哪怕街角的一隅也都是灵感来源。年龄大了,他显得矍铄,也清晰知道自己才华的局限,但灵感依旧会来找他,让他写出连自己都惊讶的句子。
搬到新居后,他有一个明显的改变,那就是签给文友的书,落款变成了“七娘山下”。我上次来是在一个下午,在黄老师书房兼工作室的阳台上,远远看过那座山,并感慨很少在南方见到这么高大的山。据说,山那边是海,隔海相望的,则是香港的山。我从没靠近过那座山,自然也没见过山那边的海。但我见过洞背的海,站在一大片的公墓里,望着远处灰色的海平面,这很容易想起法国诗人瓦雷里的名作《海滨墓园》,能够在海滨的墓园里安然散步的,除了诗人,再也想不到别的人。
现在,黄灿然与海,有了一整座山的距离。他住在一栋自建楼的三楼,楼下有个小院子,房东的恶狗正在院子里溜达,这只狗常常与黄老师的狗发生争斗,但今天显得很安静。
黄老师已经在走廊上向我招手。走上楼梯,拐进黄老师家里,一整排英文书映入眼帘,黄老师从房间里走出,问我们喝茶还是喝咖啡。说着说着,我听见房间里动静很大,原来他把自己的两条狗关在房间里,怕它们惊吓到客人。我们表示没有关系,那两只狗被放逐出来后,开始穿梭在我们几个人中间,来来回回,低头找寻着什么。之后他又带我们去看他工作的房间,三面是书,一面有个小阳台,他指着远处的漆黑告诉我,哪里是菜地,哪里是树林。
随后,我们倚靠着这栋房子的黑暗,开始坐下来喝茶。奇怪,刚刚一路过来都觉得很静,现在一落座,耳畔却浮起一片夜虫与蛙声。黄老师说城里人估计在这里会睡不着觉,他早已经习惯了。他平日里写作和翻译的工作都在这里进行,桌子上摊着最新的译稿,“是一部很厚的奥登”,他说。我翻了翻,上面用红笔圈出很多修改的地方。
我们漫无目的地交谈。最令我惊讶的是,黄老师所有的工作几乎都是在手机上完成的,他说自己很早就如此了,他觉得方便并且效率高,说着便给我们示范。他手肘立在桌子上,举着手机,下面放着一本英文诗集,低头看一句,抬头在手机上输入一句。很难想象,他那么多译作都是这样完成的。他说以前在报社下班时,常常在茶餐厅门口,或者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坐下来,开始写。他喜欢工作,每天都要工作,有次去了香港,有几天没事做,也没有带书,就非常难受,让女友在家里拍给他,他就对着照片来做翻译。他边说边一根根地抽着烟,帽子下面锐利的眼睛不时扫过我。
不知聊到哪儿,黄老师说起自己除了豆瓣,似乎没别的社交平台,我建议他开设一个小红书,那里聚集的年轻人比较多。他颇有兴趣,但想到精力跟不上,便作罢了。他说自己一直以来都是挺前卫的,上个世纪90年代起便开始用电脑写作。等到后来,他有手机后,又觉得电脑笨重,不够方便,才彻底把写作转移到了手机上。
香港导演许鞍华最新的一部作品,是一部纪录片,名字很直接,就叫《诗》,黄老师是主角之一。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也是在纪录片中反复出现的场景。纪录片里的黄灿然,与我面前的似乎没有任何区别,他的每一天仿佛都极其稳固,任谁也无法动摇。就像他说的,写作本身就是消耗很大的工作,写作者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吃的玩的用的都不需要太多,写作者与人世最牢靠的链接应该是、也只能是作品,其他的都不重要。
黄老师目光深邃地望着我,细细的烟缕从他的指缝里飘出,又在桌上的台灯的照耀里被放大了轮廓,随即在夜虫的奏鸣下,朝着窗外的七娘山飘散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