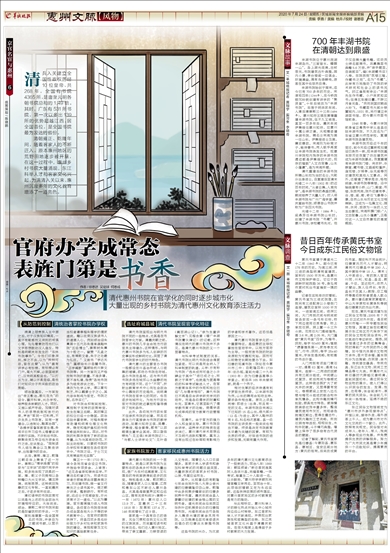|
|
插图/杜卉 |
作者/徐志达 吴定球 何志成 清兵入关建立全国性政权历经10位皇帝、共268年,全国有书院4365所,是唐至元明各朝书院总和的1.49倍。其时,广东有531所书院,第一次以多出139所的优势超越江西,居全国首位,是全国书院最为发达的省份。 清朝雍正、乾隆年间,随着客家人的不断迁入,原本惠州地区的荒野田地逐步被开垦,在这一过程中,惠州乡村书院大量涌现,东江科举人才和客家文化兴起,为满清入关以来,惠州沉寂多年的文化教育增添了一道亮色。 从防范到控制 清统治者掌控书院办学权 满清上层贵族入主中原之后,对于汉族知识精英,一直怀有敏感而又深刻的戒惧心理,处处着意防范他们以文字思想鼓动汉人造反。特别是明朝末年发生的“东林书院事件”,令他们印象深刻,挥之不去,以为“种种可恶,皆在此辈”;认为“盖有讲学必有标榜,有标榜必有门户,尾大不掉,必致国破家亡,汉宋明其殷监也。”以打压为主,辅以怀柔笼络,是他们对知识分子所采取的政治策略。 顺治登基后,一方面发出“帝王敷治,教化在先”的诏令,重开科举,兴办学校,培养服务新朝的人才。同时,又施以威严手段,加强对读书人的思想统制和言行约束,声言“军民一切利病,不许生员上书陈言,如有一言建白,以违制论,黜革治罪”。“各提学官督率教官生儒,务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着实讲求躬行实践。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他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限制读书人结社集会以及聚徒讲学、出版著作的自由。 此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总体上秉承了这一方针。康熙以“博学鸿儒”的招安与“文字狱”的恫吓两手并施,较多地体现了阴柔的一面。雍、乾父子则竞相以各种藉口大兴文字狱,镇压异端,统制思想。这种疯狂残暴的文化专制,一直到嘉庆之后,才逐步有所收敛。 清初诸帝的书院政策可以说是与上述的社会政治大环境相呼应的。大体说来,顺治、康熙二帝对书院采取的是阳誉阴抑的手法,一方面批准建复一些全国有名的书院,并亲自为之题词书额,以显示当权者遵奉程朱理学的儒家道统,藉以收束汉族读书人的道德人心。例如顺治诏朱熹第十五代孙朱煌承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康熙封朱熹为十哲之一,誉赞“孔孟之后,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为弘巨。”又御书“学达天性”匾额给长沙岳麓书院,“正学阐教”匾额给杭州崇文书院等;另一方面则又严格控制书院的数量,不准多建,更不准私建。指责“各地书院多为结党游谈之地,下令一律改为社学义学,课以章句制艺,所以羁縻士子之心,其内容体制纯为官定。书院之制,名存实亡”。 对书院由抑制到控制、寓控制于支持的政策转变,发生在雍正后期。其时雍正的权位已经十分稳固,政治经验丰富老辣,对程朱理学有助建构纲常伦理文化秩序,稳定和维护皇权的作用有愈益深刻体认。因此,对书院的利弊存废有了新的政治考量,认为与其被动防范,不如主动控制,只要把书院的办学权牢牢掌控在各级官府手中,“书院之设,于士习文风有裨益而无实弊”。 雍正十一年(1733年),谕令各地在省会设立书院,并拨给专项资金。上谕言:“近见各省渐知崇尚实学,不事沽名钓誉之为,而读书应举者亦颇能屏去浮嚣奔竞之习,则创建书院,择一省文行兼优之士读书其中,使之朝夕讲诵,整躬砺行,有所成就,远近士子观感奋发,亦兴贤育才之一道也。”以此为肇端,官方高调强力进入书院建设,各级官办书院很快被办成全国各地大小不等的学术教育中心。在官府的鼓励扶持下,府县四郊乡邑也纷纷致力于乡村社学和家族书院的建设,承担起普及文化知识的基础教育任务。 选址府城县城 清代书院呈现官学化特征 清代书院呈现出与明代书院不同的一些特点,尤其是在书院官学化方面,清嘉庆朝之前,惠州的书院几乎全由地方行政官员主导建办,这种情形,与明代惠州书院多为私人创辟的历史事实形成鲜明对比,突显了清代书院官学化的时代特色。 清代惠州的主要官办书院一般都设在州县治所或人口密集的墟镇,即府办书院在府城,县办书院在县城,这与宋元明书院多选在城郊山水幽静的地方有明显不同。这个“不同”,折射出教育学术中心向社会政治中心靠拢的历史趋向,说明清代书院在官学化的同时,也在逐步地城市化,为地方行政长官对书院的就近掌控和督导提供了地利条件。 此外,各级地方行政长官不但亲抓书院的创建,而且还身体力行直接参与书院的教学活动,如惠州知府王煐、吴骞、伊秉绶、程含章等,都有“以政暇课生童学业其间,因以登临啸咏”(见王煐《丰湖书院记》),“与都人士讲学论文”(见叶适《奠丽湖山记》),“亲为生童讲解文字”(见程含章《增广丰湖书院膏伙碑记》)的记载,这种情况在明代的惠州书院并不多见,是清代惠州书院的又一个显著特点。 与科举考试制度的关系,清代书院比明代书院结合得更加紧密,可以说是完全纳入了科举制度的轨道。义学(亦有称为书院)“选未成而可造之小子肄业于其中”“进已成之士,而教之于庠序”,也就是为更高等级的科举考试输送人才,在官方教育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已经“几与儒学相埒”。清代书院已不再是自由讲学研究学问的场所,而是各级儒学的附庸和补充。至清末,它甚至取代了儒学教书育才的功能,使儒学退化成单纯的官方教育行政管理机构。 在清代,由于官方的强力介入和全面主导,惠州书院自由讲学、涵养学术的特质在逐步消亡。惠州清代学术思想远不及明代活跃和繁荣,基本上没有出现过在岭南较有影响力的学者和学术著作,这恐怕是原因之一。 清代惠州书院官学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经费的主导权掌控在官府手中。以地方官府为主导,一般而言书院的财政来源较为可靠和充裕,因而可以较稳定长期地营办下去。如归善的观澜书院(院址在今惠州市二中)自乾隆四年(1739年)创办起,直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改为归善县高等小学堂止,前后共165年未曾间断,就是一个例子。 相对优厚的经济待遇有利于罗致优质师资。以丰湖书院为例,山长的聘用由知府主持,要求条件相当高,原则上须是两榜(即进士)出身,而且有一定的文名。丰湖书院自宋湘以下已知的15名山长,绝大部分(12名)为进士,其中入翰林的有8名,科名档次甚高。县一级书院的主讲资质一般来说也相当不错。师资是决定书院教育水平最为关键的因素,有较为优质的师资,对促进书院的进步和发展,无疑有重大作用。 家族书院发力 客家移民成惠州书院活力 清代惠州书院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以家族书院为主要形态的各类乡村书院大量出现,使广大农村远离教育、文化落后的传统面貌得到逐步的改变,特别是进入雍、乾时期以后,随着客家人口从福建、江西和粤东山区不断迁入惠州各县,尤其是海禁复界区和边远山区。据有关资料统计:康熙十一年(1672年)惠州总人口13.9万,至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发展到137.4万,146年间增长了近9倍。 客家是一个具有自己的语言、风俗习惯和自我文化认同的汉族民系,历来重视读书和科举功名。他们迁入惠州地区,带来了崇文重教、力耕苦读的人文传统。随着迁入人口日益增多,客家子弟入学读书和参加科举考试的问题日益突显,大量宗族式的客家乡村书院、山房、书屋应运而生。 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乾隆七年由当地叶姓八大房公尝兴建的归善镇隆仰岱山房,乾隆中由多祝蔡步蟾首创的归善多祝养中书屋,嘉庆年间由县人廖肇衍创建的紫金桂山围的文明书舍,道光年间由马来西亚华侨叶迈帆捐资创办的归善挺秀书院,光绪年间由古竹各姓乡人集资兴建的紫金凤岗书院,以及晚清名臣邓承修退休后倡办的归善淡水崇雅书院等。 这些书院的兴办,为沉寂多年的清代惠州文化教育添注了一股新活力。同治八年(1869年)朝廷颁谕:“新迁客民准其附入各该州县,另编客籍,一体考试,每童生二十人取进一名,以示鼓励。”惠州府学学额则另增客籍文学两名。至同治十年,此项临时增额又定为永远实额。这些扶持政策的颁布落实,对惠州客家地区的乡村教育更是有力的推动。 与此相呼应,惠州科举人才的孵化热点开始从中心城市向边远山村转移,东江客家科举人才不断涌现,并表现出家族性和密集型的态势。东江流域客家文化兴盛于清嘉庆前后,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乡村教育的大力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