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应征 六月,明媚而忧伤。阳光炽热明亮,照亮每一个风尘弥漫的角落, 风儿穿越岁月,撩拨记忆的琴弦,所有的过往,悉数而来。 洁白的栀子花盛开在校园,我与多年同窗告别,各奔东西。火红的凤凰花怒放在南国,我送别一季又一季的学生,教室里依然坐满了人,但不再是原来熟悉的面孔。 六月,有可爱的儿童节,有父亲陪伴的日子,简单朴实快乐,我们在按时长大,父亲在如期衰老,我们渐行渐远。没有父亲的儿童节,我已长大,与父亲一起离去的还有我的天真与童年。 六月,有父亲的生日,那是六月送给我们家的厚礼。多年来,这是我们家最隆重的节日,亲朋好友会来祝贺,我们可以尽情享受平时吃不到的食物,可以见到难得走动的亲戚,我们小孩子可以趁大人忙碌更疯狂玩乐,这天的热闹不亚于春节。可没有父亲的生日,只能看着相片,听着父亲生前留下的视频与录音,回味从前的快乐。没有父亲的父亲节,只剩怀念父亲的点点滴滴在记忆里生根发芽。 印象中的父亲,中等个子,眉毛浓黑而整齐,大大的眼睛神采炯炯。父亲性情和善,特别爱笑,一笑就露出那歪七扭八的牙齿,庆幸的是这些不守规矩的牙齿没有向外凸出,也就没有影响父亲的阳光帅气,爱美的大姐最喜欢别人说她长得像父亲。父亲从不在我们面前吹嘘他传奇的历史与荣耀,我们是从表姐堂姐那里了解一点点,从母亲压在木箱底下的奖状奖章知道一点点。 父亲是个老顽童,是一片生产趣味的土地,是一个盛放快乐的摇篮! 寒冷的冬夜,只要母亲回娘家,父亲就带我们以及表姐堂姐一起掏麻雀。在以农业为主的乡村,麻雀太多总是不太可爱的。它们总是将巢安筑在屋檐下,茅草屋也因此被老鼠与麻雀掏出一个个洞,雨季一到,屋内就细雨纷飞。漆黑的寒夜,丝丝寒意侵入骨髓,但寒冷阻挠不了我们贪玩的心。我们等待天黑麻雀入睡后,搬来家里最高的凳子,兴奋地跟在父亲身后。父亲带上手电筒,悄悄来到屋檐下。他站在凳子上,用手电往屋檐的茅草洞里照。强烈的光毫无预期地闯入,麻雀惊慌失措,叽叽喳喳乱成一团,机灵的老麻雀想飞出来,但出口被父亲挡住。有时洞很深,弯弯曲曲,父亲就只能伸手去掏,可这种掏法很盲目,充满了惊险刺激,有时会掏出老鼠,最恐怖还是那次掏出一条冻僵的小蛇,引得我们阵阵惊叫。 偶尔,点上一盏油灯,我们围坐一起,父亲领着我们玩瓢无姑的游戏。父亲将米铺在桌上,厚厚地均匀地平铺,用两根筷子支撑着一个大瓢,由两个人扶着筷子往前运动。你可以先许下愿望,如果能实现,那瓢无姑就会自觉往前走,如果不能,它就不走,就这样来预测未来的事情。 在我们家,每天最热闹的时刻就是吃饭时光,父亲与我们会聊起各自读过的小说故事。从《三国演义》《杨家将》《水浒传》《封神榜》《上下五千年》到当时流行的《七剑下天山》《射雕英雄传》,甚至琼瑶三毛亦舒的言情小说,我们聊得唾沫横飞,争得面红耳热,这时,只有母亲出场镇压,才能暂时休战。 我们父女之间,我对父亲最初的记忆停留在隆冬。天空飘着大雪,地上已积了厚厚一层,伯父的继子娶媳妇,娶了朱家聪明漂亮的哑巴。等到父亲主持完婚礼,疯狂一天的弟弟已经熟睡。父亲背着弟弟回家,又来接我回家。我趴在父亲的背上,看到白茫茫的天地中,片片雪花在空中旋转飞舞,听到父亲深一脚浅一脚踩在积雪上咯咯吱吱的响声,我总觉得那晚的路特别漫长,父亲的背特别温暖,值得我用一生来回味! 几时,每逢过年,我们姐弟争着去外婆家,我争不过他们。但父亲去外婆家都会带上我。 那时,父亲与外公舅舅等亲友打骨牌,我就在附近的床上睡觉。第二天早上,打牌的大人还在熟睡中,我就起床了。没事可做的我就会去打扫卫生,把他们打牌的残局收拾好,再去打扫每个房间,或帮外婆烧火做饭。因此,从小的我就获得了勤快机灵的殊荣。 上小学的一天,父亲来学校找我,想放学后带我去朋友家吃饭。邓小飞老师热情地领着父亲出现在教室前门,因为逆光,父亲古铜色的皮肤更加黯淡。平时不读书的李正伟马上看到了我父亲,他戏谑地叫嚷:“哪里来个雷公?”我循声一看,是我父亲,我瞪着李同学,大声回应:“是你爷爷!”同学们哄堂大笑,李同学有点难堪又不敢再发声。 六月的黄昏,暴风雨突袭,放学后的我们龟缩在初中教学楼下,我们望天长叹,诅咒着暴风雨,祈祷着风雨快停。好不容易等到雨势稍小,我们几个伙伴相约冒雨回家。虽是六月,雨落在头顶,滴在身上,浸透单薄的衣衫,风儿吹过,顿生丝丝寒意,可这阻挡不了我们回家的热情。在刚出校门的小桥上,我惊喜地看到迎面而来的人是那样熟悉那样亲切。湿漉漉的衣裳紧贴在他瘦弱的身体上,雨水顺着他的发梢流下,又从下巴处滴落,可风雨无法撼动他那坚定的目光,那目光里蕴藏无尽的温情与慈爱。 那,就是我的父亲,被淋成落汤鸡的父亲! 他踩着单车,单车前面挂着两把大伞……经过暴风雨洗礼的父亲像铁塔一般矗立在雨中,在我心中巍峨成一座大山。 那一个寒冬,患有多年哮喘的我,半夜高烧,浑身发烫,呼吸十分困难,整个房间都听到我沉重艰难的喘息。父亲见状,把我用被子包裹起来,放在单车上,他在前面推车,二姐在后面扶着我,我们三个沿着大堤缓慢前行。深夜的乡村一片漆黑。夜,静得可怕,偶尔传来几声狗吠,还有单车的吱嘎声与我老牛般的嘶喘声。我们摸索着前行,一路坑坑洼洼,我们摇摇晃晃,跌跌撞撞地挪出两三里,来到大堤外,周立奎老医生的家里还亮着一盏桔黄色的灯,灯光微弱,却给人无限温暖与希望。父亲叫醒老人,周老医生说,这是急性肺炎,如果再迟来几个小时,就没有命啦! 读高中时,我去了市里最好的三中读书,距家有40多里路,父亲踩着单车,将我行李绑在单车右边,再载上我,沿着弯弯曲曲高高低低的石子路,一路颠簸着来到三中。到了学校后,又带我去街上买了一双红色的保暖鞋,从此那个冬天的记忆是可爱的红色。
-
即时新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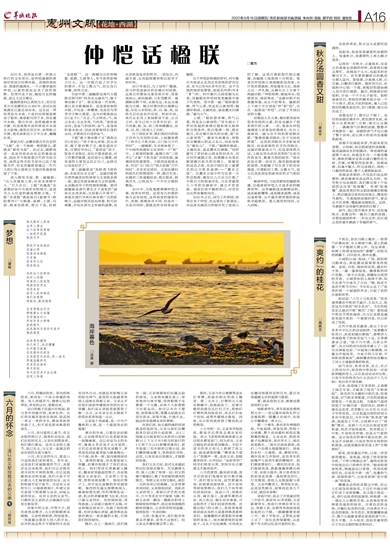
六月的怀念
——谨以此文献给我远去的父亲(1)
来源:羊城区域
2022年09月16日
版次:ZHA16
栏目:
作者:胡应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