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明 暮春的邮差总爱迟到。等了一季的泡桐花却在某个晨雾未散的时分,忽然把淡紫色的信笺投递到青瓦檐下。那些花瓣原是蜷成婴儿拳头般的骨朵,裹着灰褐色绒毛,像是裹着旧报纸的糖块。某夜细雨掠过瓦垄,它们便趁着月光舒展,将绢帛般的花瓣层层翻开,露出喉间缀着金粉的蜜腺,引得野蜂醉醺醺地撞进花芯。 小时候家乡的泡桐树特别多,每个村子里都有。泡桐树树干笔挺,直插云霄,庞大的树冠肆意铺展,像撑起一把把巨伞。它们生长速度飞快,栽下后不费太多心思就能茁壮成长,材质轻巧实用,用途极为广泛,自然而然成了村民们的心头好,房前屋后都喜欢栽上几棵。 “一树风铃一树春,桐花不语叹春深”。每至春日,泡桐树还未长出叶片,枝梢上便已簇拥着一簇簇泡桐花。串串花儿悬在枝头,活脱脱一个个小铃铛,每一枚都是由五片薄如绡的花瓣拼成。清晨,露珠在花瓣的褶皱处凝聚,成了晶莹的珠串;风起时,“叮咚”坠地,在青石板上洇出深紫色的句点;花开最盛时,整棵树像是浸在绚烂的霞霭里,连砖缝中钻出来的蕨草,都沾上了几分淡紫,好似被揉碎的绮丽词句溅了满身。 泡桐花的边缘紫中泛白,像极了少女轻盈的裙幅,又似一个个小巧的喇叭。它们一簇簇紧紧相拥,叠成一座繁花堆砌的塔,有的洁白如玉,有的浅紫如梦,有的略添几分深沉。满树繁花盛放,馥郁的香气肆意弥漫。泡桐花的芬芳淡雅宜人,远远就能闻到,清新中裹挟着丝丝甜润,淡香里又藏着一抹青涩。它们远离尘世喧嚣,默默绽放,将自己热情奔放的性子尽情释放,或白或紫,超脱于世俗之外,尽显悠闲宁静之态。 祖父总会找来竹篙,帮我勾下低处的花枝。我轻轻用指腹摩挲花瓣背面细密的茸毛,那触感竟与蚕房匾箩里安静眠着的蚕宝宝极为相似。花萼处渗出黏黏的花蜜,放进口中一尝,是被阳光烘晒到极致的甜,还带着一丝独特的腥气,奇妙的是,这味道竟与蚕蛹在沸水中翻滚时散发的气息交融在一起,形成一种别样的味觉记忆。当蜜蜂扇动翅膀的嗡嗡声透过窗棂传进来时,蚕儿们正弓着翡翠般的脊背,一点点将桑叶啃出如镂空诗行般的形状。 教室前,也有一棵高大的泡桐树。粗糙的树身上,被顽皮的孩子们刻划得伤痕累累。在那干裂的沟壑里,树脂裹挟着去年的柳絮,缓缓垂落。正午,日光斜斜切过树冠,那些琥珀色的“泪滴”便折射出七彩光晕,仿佛老树用棱镜精心誊写的彩虹体回信。我时常望着窗外发呆,泡桐树上小鸟欢快的啼鸣,总让我忍不住地走神。 “树荫如盖遮炎暑,花穗如烟胜紫鹃”,老宅的泡桐仍按时抖开满树信笺。凋落的花瓣总爱栖在井台边的陶瓮沿上,将倒映的云絮染成紫棠色。南风吹过时,那些悬在空中的风铃便簌簌翻动纸页,把四十年前的蚕沙香、树脂泪和玻璃糖纸的脆响,都摇成细雨般的标点,轻轻缀在春末未完的信尾上。
-
即时新闻

桐花笺
来源:羊城区域
2025年04月18日
版次:ZHA12
栏目:
作者:杨志明
分享到微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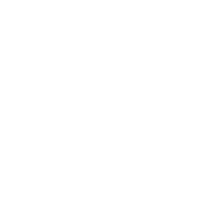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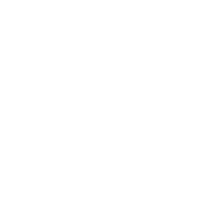
使用"扫一扫"即可将网页分享至朋友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