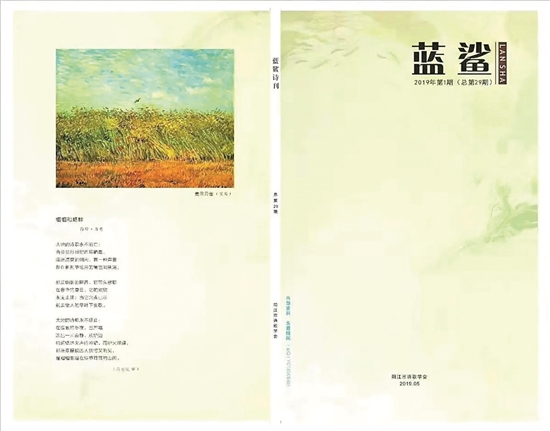
|
|
|
□林贤治 以诗的形式编写地方志 多年来,每年都会收到一些从各地寄来的诗刊,使我得以熟识《诗刊》的围墙之外的许多年轻的面孔,听到他们或押韵或不押韵的声音。后来,刊物少了起来,打听之下,才知道陆续停办了。我编过刊物,深知此中的艰难,仅筹措资本一项,便足够逼退天真烂漫的小诗人了。但有一种诗刊,近二十年从未间断,每期准时到手的,就是《蓝鲨》。 在我的家乡阳江市,有十来个写诗的青年凑到一起,成立一个小小的蓝鲨诗社,算是有了自己的园地。《蓝鲨》长开本,质朴、大方,却也不失雅致。随着岁月的推移,诗刊日渐变厚,不少外省的诗人也参加进来了。刊名很好。蓝鲨,作为大海的族类,野性难驯,始终向往运动和无限。 诗社发展起来以后,陆续编书出版。我曾收到几种多人合集,日前又收到新编的一种:《阳江诗志》。故园的风物,青春的歌咏,教我非常喜欢。 以诗的形式编写地方志,就我所见,在全国恐怕还是第一部。地方志记载地方的历史、地理、民俗、文化、生产和生活等,它是记录性、实证性的,巨细无遗。“诗志”则取人文的部分加以扩大,它是阐释性的,诗性的,审美的,多出一层情感色彩。 地方叙事灌注深情 叙说阳江本土,对诗人来说,无需依赖典籍和传说。他们生于斯长于斯,完全可以从生活出发,从个人的生命体验出发进行书写。许多诗人直接歌唱出生地,那里的田野、村舍、牲畜,种植的各种作物。陈计会的《报平村》,写城镇化带给农村的变动是典型的。推土机倾泻如血的红泥,覆盖大片水稻,“遗留下/一望无际的风,以及/疯长的野草,没有牛哞的春天”,全篇充满痛感。作为现场的目击者,诗人袖手,沉默,有笔瑟缩在衣袋里,嗫嚅如听鼠嚼。他无力制止,自责为“同谋”,表现出少有的批判的勇气。黄远清写海边修建的火力发电厂,“把煤换成光明”,却不得不以污染海水和空气,毁灭鱼类和红树林,甚至直接付出居民的健康为代价。生态环境的保护,是伴随几十年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产生的,普遍存在的严重问题。对此,诗人同样显得很无奈,最后写道:“母亲靠在岸边发呆/好多年以前,海蜇和鱼虾/常在她脚下亲昵/如今,她的心事啊”。结句很好,余波未了。林枢写阳西地区的盐田,瓷片厂的旧址,还有青洲岛的破船、礁石、渔火、“北来的候鸟”,构图空旷而凄冷,感喟岁月的“刻骨艰难”。谭夏阳和容浩同时回到少年,却是两种不同的情调:或者神秘的悦乐,或者无端的怅惘,而幼小的心灵一样有着虚缈的星芒和远方。 另一群诗人,如张牛、陈舸、王洁玲、黄昌成,颜仰建等,使用“时髦时代”的形式:旅游来描述阳江的山水,各地的胜迹。由行客的状态所决定,多着意于形象的描摹和风景的组合,用笔近于油画的平涂,不像雕刻的深入,少了“土生子”身上的那种沉坠感。陈舸的《独白》是遒劲的,繁复的;诗句作长方形排列,严整有如沙积石累,凸出视觉形象,颇具匠心。 无论取何种视角,本土诗人的地方叙事,无不深情灌注。 “南海Ⅰ号”在全国是有名的。巨大的船体出土之后,让时间和辉煌停泊在博物馆里。诗集中有两位诗人写到它,面朝瓷器的方阵侧身而过,陈舸神往于打捞本身,在动荡的水波和沙粒中发现“回”字形物体,颇有点形而上的味道;冯瑞洁则在沉落海底的词语中,读到人间的创伤和寂寞,而对久远的无名的水手起了深深的缅怀。 在怀旧中讴歌时代 在伟大的废墟对面,诗人寻找另一些旧址。陈世迪的《水埒街》,黄赤影的《七贤书院》,同时注目于一种文化精神的失落。水埒街内的孝则图书馆已成危房,红砖封门,木窗破败,墙壁为爬山虎、野芋、蕨草所包围,恍如陷入幽谷。七贤书院深锁大门,“阳光喑哑,任性青苔拾级而上,长至瓦楞”,一样是绿色的荒芜。不同的是,黄赤影对未来有所期待,所以写“庭院如今容颜不再/却气度非凡”。 大约诗人是喜欢怀旧的,伤逝的。其实,追忆是人类的一种习性,可以说是基本人性之一。所以地方志有一个重要的部分留给民俗,旨在记录世代的文化智慧,使优秀的传统得以承传。 百姓的生活是日常生活,没有宏大叙事,陈世迪有诗即取名《伟大的日常》。诗人仍然以观察者的身份出现,从阳台柔弱而强韧的蕨草,写到街道两旁舒展的紫荆花树,写到络绎经过的各式各样的车辆,是一条展开的生活之链。 “大江流日夜”,浩浩荡荡,奔流入海;转弯处尤为湍急,每见惊涛。毕竟,现时代已经开启,借用马克思的话来形容:“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这是一个变革的时代,转型的时代,有破坏,有建设,世界日日在改变,或行将改变。鲁迅这样说过:“中国社会没有改变,所以没有怀旧的哀词,也没有崭新的进行曲。”而在《阳江诗志》中,却同时有着“对新的讴歌”,和“对旧的挽歌”,正好为大时代的来临做了印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