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少年叶兆言(前中)和祖父叶圣陶(前右)、父亲叶至诚(后右)、母亲姚澄(前左)及堂兄 |

|
|
叶兆言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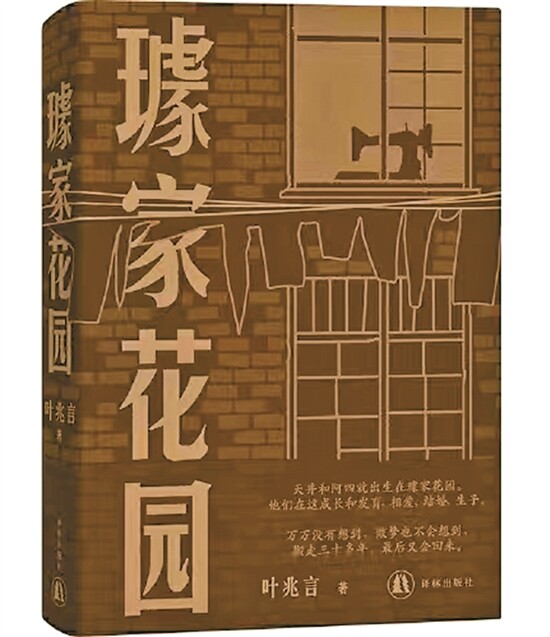
|
|
|
文/羊城晚报记者 梁善茵 图/受访者提供 “我的生命就在于写作。”对于作家叶兆言来说,40余年、七八百万字、近二百本著作,他的著作堆起来早已超过他的身高,用“著作等身”这句话来形容,并非虚夸。 除了笔耕不辍40余年的隽誉,叶兆言还出身于书香门第:他的祖父是知名教育家、文学家叶圣陶,父亲是作家、编辑叶至诚。如今,他的女儿叶子是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也酷爱文学创作。如此家学传承,在文坛并不多见。 “我祖父80多岁时,还会每天坐在书桌前写东西,一坐就是八九个小时。祖父和父亲给我的印象是,成为作家、写出来不重要,成不成名不重要,坐在那里的背影很重要。”就在日夜伏案写作的背影中,他的书一本一本地出,最新推出的便是《璩家花园》。 “璩家花园”目睹了主人公天井及一众亲朋好友和街坊邻居的命运起伏,也见证了重大历史时刻的轮番登场。这是叶兆言现有十四部长篇小说中体量最大、故事时间跨度最长的作品。 单纯靠写自己的经历写不好小说 羊城晚报:您的新作《璩家花园》的创作缘起是什么?听说您此前将该小说命名为“缝纫机,蝴蝶牌”,有何用意? 叶兆言:《璩家花园》的故事最早是从缝纫机开始的,我原想写一个关于缝纫机的故事,也就是小说开头很重要的器物——一台蝴蝶牌缝纫机。小说想通过缝纫机把一连串的故事缝起来,就像做衣服一样,但后来越写越长,发现缝纫机的名字盖不住这部小说,于是就改成了“璩家花园”。故事里讲的是乱世中的一对男女,已经走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他们选择以缝纫机作为定情之物,但后来又因为缝纫机而分开。 羊城晚报:书中的人物或事件在现实中是否有原型? 叶兆言:《璩家花园》是完全虚构的,但这部小说有点特殊,中间可能有很多我自己特别熟悉的人和事。比如小说中的费教授是我祖父的同代人,他在1970年一次性补发了7000元工资,这就是我们家的事情,我父亲去领,背了一书包钱回来。就像是雷蒙德·卡佛所说的,每个作家在写作时都免不了受自传色彩的诱惑。但单纯靠写自己的经历是写不好小说的,好小说就像好酒,需要加入各种材料和技术勾兑而成。 羊城晚报:小说里投射了哪些南京的影子? 叶兆言:璩家花园放在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座古镇,都可以打捞出辉煌的历史文化。把它放置在南京,是因为我生活在南京,南京是我坐着说话的一把“凳子”。我并非有意地强调南京这个符号,也不带有任何地方主义色彩。 描写一种过分纯粹乃至抽象的爱 羊城晚报:第一章讲1970年,第二章讲1954年,第三章又到了1971年……这部小说的整体结构是时间性、线性的,但各章节的年份是来回跳跃的? 叶兆言:我完全是从现代阅读的碎片化特点来考虑的,自由阅读以来,大家的阅读都是碎片化的,我们没有理由反对碎片化。几乎没有人是认认真真地从第一页开始读书,读一些是一些,有时候不想读就不读了。《璩家花园》的时间跨度很大,也许读者想从自己熟悉的那个年代开始看,如果觉得有意思就继续,没意思就放下——这是当下阅读的基本状态。所以我在写作的时候经常对自己说,不仅仅要把第一章写好,读者有可能从第二章、第三章开始读起。不能把精力都放在书的开头,要认真地、平平淡淡地写好每一章。也不需要把开头写得太精彩,应该考虑的不是怎样吸引读者,而是考虑别让读者找到漏洞,别写得太烂。 羊城晚报:为何设定“混沌初开”的故事开篇? 叶兆言:《璩家花园》开头写的是一个男孩偷窥的故事。在17岁以前,女性对璩天井来说只是去女厕所的人。当一个性的场面赤裸裸地在他面前展开,他在性观念方面得到启蒙,但其实他内心是恐惧的,表现出小男孩的纯真。这种写法也有一定的风险,因为有的人读了以后也会把它看作一个轻薄的故事。但其实我想写的是这个世界野蛮地、粗暴地在他面前打开,而且是伴随着祖宗的目光、几千年传统文化背景的打开。这个开窍其实是个好事,因为性也有它美好的一面,也是不可阻挡的东西。 羊城晚报:小说塑造的璩天井就是这样一种晚熟、迟钝,有些麻木的慢性子。他与当时所谓的“时代骄子”恰恰相反,为何会选择书写这种小人物? 叶兆言:我反复解释过,璩天井是一个理想化的人物。人作为一种“两足无毛动物”,在荷尔蒙影响下会释放出浓浓爱意,这是人的本能,但它很快就会消失。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能够出于本能一直喜欢某个人,并在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这种概率是很小的。 书里面的璩天井觉得自己很幸福,他能够每年到监狱探望阿四,发自本能地喜欢这个“渣女”,这在我们看来可能是虚幻的、梦幻的,但他的幸福感比一般人更强。因为他愚钝,所以他能一直享受这种幸福,而不是为了得到回报。 在某种意义上,我在描写一种过分纯粹乃至抽象的爱。但是我需要让璩天井看起来可信,所以就要给他设计各种情节,让他看起来像“脑子进了水”,让他“受伤”。再好比卡夫卡笔下的甲虫,它反映了人异化的过程,我的目的也是一样的,因为保持纯洁的爱是很难的,人人都有“渣”的一面。 碎片化阅读才是最真实的阅读 羊城晚报:您曾说《璩家花园》创造了一个新纪录——在您现有的十四部长篇小说中体量最大、时间跨度最长。在创作过程中遇到了什么困难? 叶兆言:这是我写过的小说里头最长的一部,仅此而已,没什么特别意义。可能因为这部小书所描述的时间跨度比较大,最终出版时将近30万字,其他的书大概22万字,相差也不是太大。 羊城晚报:怕不怕自我重复? 叶兆言:肯定会怕重复,我为什么想写这么多,其实是出于一种“地主心理”,希望多“圈地”而已,重复是很无趣的。我是一个绝对的反地方主义作家,我特别不愿意别人把我跟“写南京”“写民国”的标签捆绑在一起。写作就是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对一个作家来说,写作的空间和时间都不重要。写作要有乐趣,最忌讳的就是驾轻车、走熟路,所以我一直说写不下去才是最好的状态。 羊城晚报:您是否会停留在传统的历史叙事当中,还是说也会去试试碎片化写作?写作者应该如何面对时间? 叶兆言:我还没完全想好,其实我一直对“碎片化”这种提法保持怀疑。我们经常讲当下时代是碎片化的,但是我觉得自己成长的历史、所经历的历史,包括阅读,都是碎片化的。现在还有多少人会从头到尾认真读完一本世界名著?其实碎片化的阅读才是最真实的阅读,唐诗、宋词从来都是以碎片化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今天这种碎片化的阅读其实是好事,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讲,看手机就是在阅读。 写作者应该要保持乐观,因为文学是少数人真正关心的事情。我们不要以为唐人宋人都会写诗、读诗,真正“玩”诗词的人还是少数。但李白、杜甫的诗句能够流传至今,直到今天我们还在看他们的作品。所以我一直坚持写作,像五柳先生说的,“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只有努力是可以自己控制的 羊城晚报:您出身书香门第,但家人似乎对您成为作家持反对态度? 叶兆言:刚开始都不太支持。因为我爸爸被打成右派,所以他说自己的孩子绝对不能干这个事儿。他们从来没想过我会当作家,写作是我自己发掘出来的,而不是他们刻意灌输出来的。他们认为没必要硬培养一个作家,没把写作当成一门行当来培养。 大学一二年级的时候,我开始参与一些文学社团,那个时候社会上对文学的热情很高涨,所以我最初的写作其实应该说是比较顺利的。但那时还是想脚踩几只船,写写东西,做个业余的写作者。研究生毕业,我才开始决定要当作家。但写作就跟吸鸦片一样,不知不觉就上了瘾了。 羊城晚报:您小时候家里的阅读、写作氛围是怎样的? 叶兆言:我记得小时候是怎么“认字”的,爸爸在纸片上写点字给我,也不教是什么字,也可能是教了,我没记住。家里有好多玻璃门的书橱,我就拿着纸片,对照玻璃后那些书脊上的字,看书上和纸上的字哪两个是一样的。家里书架上的书是“分区”的,托尔斯泰有好多,契诃夫有一整层……在我还不懂文学是怎么回事的时候,我就知道原来那些人是作家。这预示着我很可能以后还是要写东西,但不是为了当作家。 年少时,我看到祖父坐在书桌前的背影,一坐八九个小时,父亲也如此。后来是我,自然而然地坐在书桌前,一坐也是八九个小时。无论是写文章,还是处理其他案头工作,都是以高度的热情和专注投入其中。 羊城晚报:父辈对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叶兆言:总的来讲,他们会给我传递一个信息:专注做一件事就好,认真干,要做一个有用的人。这点其实很重要,干一行就干好一行,哪怕扫个地,也要把地扫干净了。 羊城晚报:如今您的日常创作状态如何? 叶兆言:随着年纪越来越大,我感觉自己已经到了用时间来对抗无聊的状态了。现在的我工作状态不像年轻时那么好,有时候能够顺利写出来,有时候大脑疲惫写不出来,甚至坦白地说,大多数时候是写不出来的。 人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能够做喜欢的事,而我喜欢写作,也能够写作,所以我很感激自己的幸运。我也很在乎“努力”这两个字,因为我们没办法控制写出来的作品受不受欢迎,只有努力是可以自己控制的。目前来说我还是马不停蹄地写,这点还是可以自傲的,我还保持着不断学习的能力。 余华就一直跟我开玩笑,他说:“叶兆言你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写得太多,你不能写这么多,你必须学人家十年磨一剑,你没事去玩都可以,你不能写这么多。”但是写完一部长篇之后,我觉得真就是——我做不到游手好闲。 羊城晚报:您之后有何写作打算? 叶兆言:运动员总是要退役的,我也知道迟早有一天会写不动的,赖一天是一天,写一天是一天,写一天赚一天。在完成之前不太想讲,最快出来的大概是在岭南大学上写作课程的讲稿,课要持续到2025年1月。 羊城晚报:是怎么备课的? 叶兆言:我是很笨的一个人,每节课的讲稿都是提前写出来,好在我也习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