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欧阳江河 |

|
|
拉斯洛 |

|
|
滕威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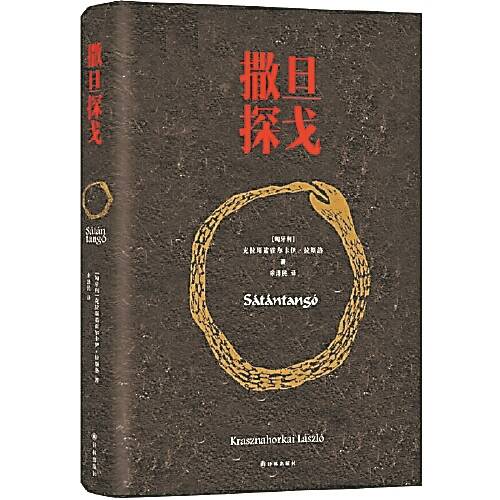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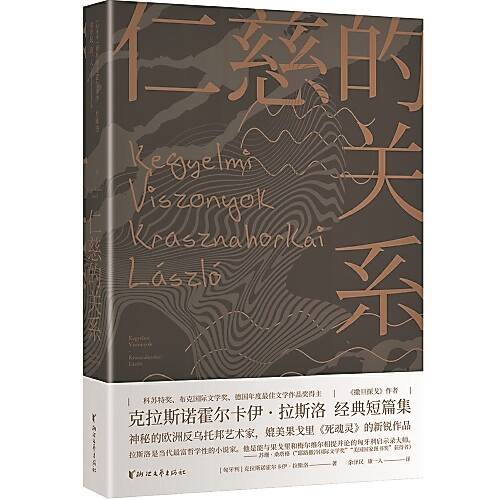
|
|
|

|
|
|
2025诺贝尔文学奖揭晓,匈牙利作家拉斯洛·克拉斯诺霍尔卡伊(László Krasznahorkai)获奖,理由是“因其引人入胜且富有远见的作品,在末日般的恐怖中,再次彰显了艺术的力量”。文坛内外又掀起了一阵热议,诺奖为何惹人关注?今年的得主为什么是他?对中国文学有何启发?作家欧阳江河、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滕威、媒体人朱又可从各自的角度发表见解—— 欧阳江河:用批判的眼光看待善与恶 羊城晚报记者 梁善茵 熊安娜 羊城晚报:您和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是怎样认识的? 欧阳江河:我跟拉斯洛认识了20多年了,具体哪一年已经忘了,但是我们见过很多次,在北京见面比较多。 我印象比较深的两次见面,一次是在2008年的柏林文学节,那年我和西川、拉斯洛三个人一起去的。当时拉斯洛住在柏林,他和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凯尔泰斯·伊姆雷是邻居,所以我们几个基本每天见面,在柏林待了六七天。拉斯洛的第二任夫人是汉学家,而且喜欢书法,所以由她来充当我们的翻译。第二次见面是2009年的第二届中坤国际诗歌奖,我作为评委,邀请拉斯洛到中国参与交流。我们每天都在一起,有过非常集中的交谈,关系也变得更密切了。 羊城晚报:您对拉斯洛的印象是怎样的? 欧阳江河:拉斯洛这个人特别豪爽开朗,特别容易相处。他和我很聊得来,我们的性格很对路,他也喜欢我的诗歌。在柏林的时候,他提到喜欢我的诗歌《玻璃工厂》,还将德国汉学家顾彬翻译的版本,跟一位德国教授皮特霍夫曼翻译的版本进行对比。他甚至背出了《玻璃工厂》里的一些句子,一字不落,说明他还挺喜欢这首诗。 羊城晚报:听说拉斯洛是“中国迷”,尤其迷恋孔子、李白,他有跟您聊过他自己对中国文化的印象吗? 欧阳江河:我和拉斯洛老是在谈李白,他超级喜欢李白,也超级喜欢老子和《道德经》。他曾经说过,《道德经》是人类最伟大的,仅次于《圣经》的文本。他读过好几种语言的《道德经》,他告诉我,《道德经》至少有50种德文翻译版本,德国不少知识分子都读《道德经》,对老子有着特殊的迷恋。 拉斯洛还迷恋杜甫,但是他最喜欢的是李白,尤其喜欢李白诗歌内部深处的豪迈、开放性以及和天地神灵沟通的方式,他说李白是创世纪的诗人,其诗歌语言创造出来的气度,是全人类独一份的。 羊城晚报:拉斯洛的中国之旅还深刻影响了他的写作,东亚文化是否为他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欧阳江河:拉斯洛作为一名作家,他的知和行、读和写是合一的。卢卡西说,“只有大作家和大诗人,才有世界观。”大作家的世界观里包含了信仰、反信仰,对信仰的抵抗以及对信仰的重新发明,甚至用批判的眼光看待善与恶、原罪与本罪,这些力量支撑一个人的写作,写到深刻的、地狱般的完美程度,拉斯洛就是这样的人。有时候偏离、错误包含着拯救,包含着赎罪的元素和力量,这正是文学所需要的。 羊城晚报:在拉斯洛获诺奖后,您说“没有那么讨厌诺奖了”,是因为拉斯洛的获奖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诺奖的“文学标准”提高了吗? 欧阳江河:现在每年出这么多的小说,销量这么大,各种故事娓娓道来,还有很多作品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可供人们消遣消费的读物太多了。但是我要问,最稀少的、含金量最高的文学有多少?我们必须保证这样的文学的存在,这是我们的历史使命。拉斯洛的文学,关乎的不仅是反抗,不仅是抵抗,他比这些还要高,他是建构,建构了什么是伟大的文学。这也说明了伟大的文学一定是一场“事故”,一个“错误”,然后纠正过去我们认为是正确的实际上是平庸的文学。 羊城晚报:是否会担心长难句给读者带来的阅读障碍,从而影响流传度? 欧阳江河:当然,对普通读者来讲,长句在智力上也好,在阅读习惯上也好,都会带来一种考验、折磨甚至是冒犯。但是没关系,我觉得必须要有复杂文学的存在,它是极少的东西,但必须有它,这是我们的使命。 写复杂文学的人本来已经做出够多的牺牲了,牺牲了版税、市场。献身于复杂文学,献身于这种比较困难的、得不到承认的东西,没关系,这是宿命。即便有些人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咒骂,没关系,让我们共同见证这种文学的存在,这是最重要的:文学有些东西得以不同的方式存在。 如果没有卡夫卡,拉斯洛就不会想到当作家 □朱又可 拉斯洛之广为人知,产生世界性的影响,应该与塔尔·贝拉导演的由他的小说改编的电影有关,但在2011年的电影《都灵之马》之后,二人就没有合作了。无论如何,即便是在诺奖盛名之下,拉斯洛仍然属于一个“小众”作家。看网络,说是一夜之间因为诺奖的加持,拉斯洛的中文译本订购量增加了上万本,这个数字和董宇辉前两年的“直播带货”销量比起来,好像也没有多少值得夸耀的。可见,文学在数字时代真的失去了社会轰动效应。说到电影与文学的关系,我想,莫言的获奖,与张艺谋的电影《红高粱》风靡一时也不无关系。不必迷信那些评委真的就是细读文本、心无旁骛的专家,他们受大众媒体的影响也不可低估。 2018年9月,我去匈牙利采访中国诗人杨炼,顺便采访了拉斯洛。见面“暗号”是:他站在小广场的路口,戴一顶大沿黑色礼帽,大高个子,说我一眼就会认出来。果然是那样。他带我进入他预订的他常去的那家咖啡馆的固定角落,他自己点了一杯咖啡,推荐我品尝当地的一种杏子酒。他说话的方式就像他的小说语言长句子一样,也和贝拉的电影的长镜头一样,一口气讲很长。这种谈话的长句子,并非单调,而是有一种音乐式的韵律,这也许与他会弹钢琴和拉二胡有关。他语速比较快,这一点,并不像他跟贝拉的电影的那种加强的自然主义式、颇需耐心的“缓慢”。“诗到语言为止”,他的语言方式,使他在表现泥泞破败的乡村、巨怪般的马戏团的鲸鱼标本、屈辱受伤的马、末日来临前的人的孤独荒凉等意象时成为一位晦涩难懂的“复杂”作家,他的现实主义似乎就是以那样超现实的方式呈现的。 他和匈牙利的文学圈子保持着距离,甚至格格不入,更多地是以自由、流散状态待在国外。给我当翻译的是曾任多年匈牙利驻北京的商务人员毕罗万。在采访中他说,如果没有卡夫卡,他就不会想到做作家;他的小说《撒旦探戈》偏离了当代匈牙利的文学传统,与匈牙利作家习惯使用的语言越离越远,这可能与他很小就搞音乐有关,他能演奏多种乐器,连二胡都拉过,还会吹埙。1999年,拉斯洛还曾选择追随李白的足迹游历中国,后来写下游记《只有天上的星辰》。 采访完拉斯洛回到布达佩斯,跟杨炼说起这次采访拉斯洛,杨炼说,拉斯洛和他是老朋友了,二人第一次见面是1991年在瑞士,他们是同一家出版社的作家,他们还一起看了拉斯洛7个多小时的电影《撒旦探戈》。拉斯洛当年步李白足迹漫游之前,还专门来慕尼黑和在那儿的杨炼长谈,之后他去中国,采访了杨炼的父亲、北京老字号吉祥戏院的少东家。杨炼还介绍他认识了诗人唐晓渡、书法家曾来德。 9月上旬的采访,三个多月后的12月中旬才发表,也至少说明,拉斯洛当时不是一个热门的作家。谁也不会想到,7年后,诺贝尔文学委员会把这顶世界性的桂冠给了他。 滕威:中国作家获奖与否并不取决于翻译 羊城晚报记者 梁善茵 熊安娜 羊城晚报:为什么会有所谓的“诺奖情结”一说? 滕威:80年代,诺贝尔文学奖就成了一个重要的参照。获得这个奖项的作家,通常被认为拥有广泛的世界读者群和评论界公认的创作成就。通过译介他们的作品,我们得以最快地找到与西方现代文学对话的路径,进而革新我们自己的文学语言。中国开始关注诺贝尔文学奖,是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改革开放的进程同步展开的——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层面。 到了第二个层面,也在80年代,中国的文学创作有了多元的努力和革新。一个问题自然浮现:是不是该轮到我们获奖了?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种期待变成了一种“焦虑”。如今的诺贝尔文学奖,更像是一个媒体和出版界的“事件”,大家借此热闹一番。但若从整个社会的热点来看,它其实现在已经是一个非常小众的话题,热度通常维持不过三天,很快就会被下一个热点取代。 羊城晚报:您怎么看待诺贝尔奖? 滕威: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大多数情况下并非横空出世,他们往往已有长期的作品积淀与声名积累。此外,诺奖有时也带有“追认”的性质——作家或许已过创作盛年,近作水准不复从前,但由于年轻时曾写出过伟大作品,仍可能在晚年获奖。 相对来说,大众对诺贝尔文学奖还是有一定的认可度的。当然,有些年份的获奖者争议较小,比如今年的获奖者拉斯洛;而有些年份的获奖者,比如鲍勃·迪伦、韩江,就引发了广泛讨论。这些争议,有些是有道理的,有些其实是各种霸权和偏见,比如种族偏见、性别偏见、大国对小国的偏见等等。这些争议其实带出来很多的傲慢。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讨论,而不是简单地否定。有网友说,它成了一个选书的工具。 羊城晚报:如果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中没有精通中文的人,中国作家是不是就很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了? 滕威:一部作品需要经过多种语言的转译,我们常说中文博大精深,那些语言中的精妙之处、丰富的言外之意,究竟有多少能在层层翻译后被保留、被完整传递?在翻译过程中,一定会出现“改写”。在翻译中,我们注定会丢失许多东西——那些难以转译的语言特质、文化意涵与审美韵味。因此,任何翻译都必然带有译者的主体性,受到其审美偏好、文学观念、历史认知乃至政治立场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是否有“绝对忠实”的译者,能够将中国文学原汁原味地呈现给瑞典学院的评委们?我觉得这也不太可能。 有懂中文、尤其是对中国文化、中国文学有兴趣的评委当然好;不过,随着中文在全球范围内的地位提升,愿意学习中文、理解中国文化的人越来越多。再加上AI的出现,大幅提升了语言学习和文化交流的效率。也许评委懂不懂中文不是决定性的。即便有一天,翻译不再是障碍,诺贝尔文学奖就会颁给中国作家吗? 有些时候,问题并不在于我们做得不够好,而在于对方可能有意不让我们“上桌”。我觉得这不是翻译能解决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