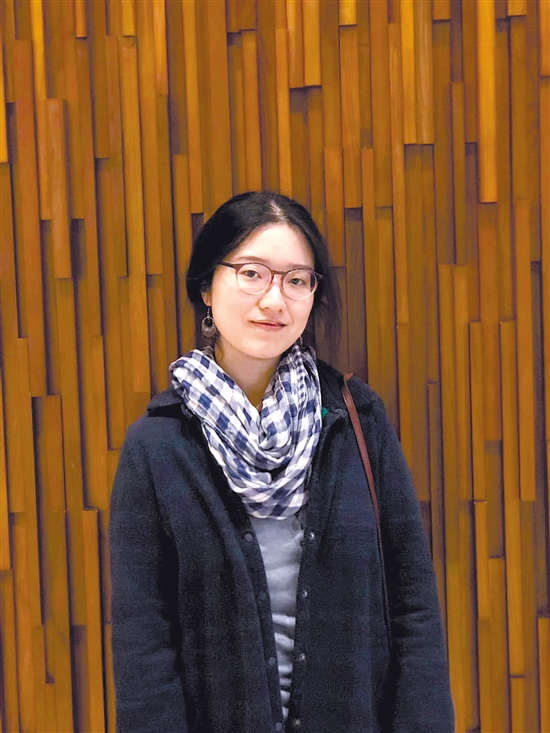
|
|
|

|
|
|
□李泽凡 李懿 1993年生于澳门,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澳门笔会成员。曾发表小说、散文、诗歌,有作品连续多年被收入《澳门年度文学作品选》。 科幻比单纯幻想更深刻 李泽凡:您是因为什么样的契机开始写作的? 李懿:抛开每次语文考试都必须写的作文外,我第一次真正的写作,是在中学的一次暑假里。当时,我的语文老师要求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创作出一本作文集。也就是在那时候,我萌发了“写出一个故事”这样的想法,于是写出了我人生中的第一篇正式的短篇小说,讲的是爱因斯坦在未来世界复活的科幻故事。也正是因为我的母亲很喜欢那篇文章,所以我才对写作产生了好奇与向往。 李泽凡:从第一篇小说开始,您对于科幻主题一直抱有极大的兴趣,为什么? 李懿:早期的时候,我之所以喜爱写科幻主题,是因为科幻故事允许人在写东西时跳出现实框架,随心所欲,不需要太多的顾虑与设计。不过后来,在阅读了更多的科幻作品、观看了更多的科幻电影后,我意识到,科幻其实可以比孩童的单纯幻想更为宏大、更加深刻。科幻主题很多时候,重心是在于讲述人类在未来会遇到的种种困境:在想象的未来里可能会进行的沉思。这样一来,虽说情节确实超出现实之外,可故事的核心依旧在人身上。科幻,或者说软科幻,实则还是人的故事。比如,我在读大学前写的一篇短篇科幻小说,《珍珠从天而降》,说的是资源枯竭的地球上,一个女人和一个机器人,在诗歌协会聚会时相遇并相爱。虽然它有着不同于现实的科幻外壳,但说到底,它仍是一个孤独者的爱情故事——因为这才是我想去探索的东西:孤独和爱情。 考虑到环境对人的影响 李泽凡:作为一位九零后写作人,您的写作带着您这一代人什么样的印记? 李懿:一个人无法代表一个群体,更不用说一整代人,而我的写作,是建立在我的所见、所听、所闻和所想之上的。因此,我只能说我写出的东西中,或许是有一些与我相似的人的影子。 九零后现在大多已经离开校园,却还未完全到成家立业的阶段。在这个时期,我们不可能不对自己的生活感到迷茫:一方面,我们已经不再是被百般挑剔又小心呵护的孩童,现在人们关注的重心已经转移到了零零后身上,而我们也终于要接受自己已经成为“大人”的这个事实;另一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新的应对机制,从而以一种更成熟的态度去面对生活,甚至在这尴尬的适应期里,开始面临失去理想与存在意义的危机。独身一人的青年在异乡朝九晚五,下班后,于窄小的出租屋里一边吃外卖一边看手机,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典型九零后的生活。而我现在想要描绘、探究的,正是这样的一个群体。 李泽凡:您出生于澳门,在上海读大学,所处环境的转变是如何影响您的写作的? 李懿:澳门和上海是两座截然不同的城市。澳门是我的家乡,家乡给予了我极大的安全感。每次我离开澳门时,都不会有依依不舍的情绪,因为我深知最后还是要回到这个地方来的。 但上海也并非那样陌生。我父母年轻时是在上海生活,在家里交谈也经常会用上海话。虽然在读大学前,我从不曾正式在上海生活过,可当我真正是一个人在上海学习、居住时,我并没有什么彷徨不安的感觉。城市是我熟悉的城市,语言也是我能听明白的语言。 然而,我的确感觉到了两座城市之间的巨大差异。这一点也的确影响了我的写作。在澳门时,我关注的主题多是人本身,比如爱情、欲望、矛盾,等等。来到上海后,我慢慢发现,大城市的人是活在一条金河里。没什么是比满是摩天大厦的不夜之地,更能激发出人的物质欲望的。上海是一个环境决定人而非人决定环境的城市。怎样在现代都市的巨大阴影下生活,成为了所有都市青年都需要面对的问题——不管他们自己有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这样的现状也确实改变了我的写作方式,使我在写故事时,也会考虑到周遭环境对人的行为与决定的影响力,而不再是像以前一样,让角色们仅凭一腔热血行动。 懂得“乡音”对人的重要性 李泽凡:那么,地方语言的变化对您的写作会有什么启发吗? 李懿:在澳门,我会因为能听懂路人的上海话对话,而产生一种隐秘的快乐;同样的道理,若是在上海的街头能听到有人说粤语,我也会备感亲切。在这之前,我从来不曾有过在写作时用上地方语言的想法,但开始在上海生活以后,我才真正懂得“乡音”对人的重要性:群体意识、自我定位和人对于地方文化的归属感,这些都是地方语言能引导人去思考与感受的事情。 在写《扁平人》的时候,我尝试去描述一个在澳门生活的上海人,因为粤语不好,在日常生活中备感尴尬,甚至觉得自己是被这个地方排斥着,仿佛一个卡在嗓子眼里的异物。我曾与一位广东朋友有过这方面的交流,他坦言自己完全无法理解或喜爱所谓的“中原文化”;我也曾和一位上海的朋友有过类似的讨论,他也同样对“北方”不抱有好感,悲观地认为上海话与上海文化已经濒临失传。尽管后者所坚守的东西,在前者看来其实是入侵自己家乡的外敌,但两个不同地方的人,居然有着同样的顾虑与担忧,虽说地方与文化背景不同,同一代人所关注的,实则是同样的议题。然而我们相互间,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分歧,我们的生活也可能因为文化认同感,有着某种轻微的错位,这样的现象使我觉得十分有意思,也是我现在最感兴趣的小说主题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