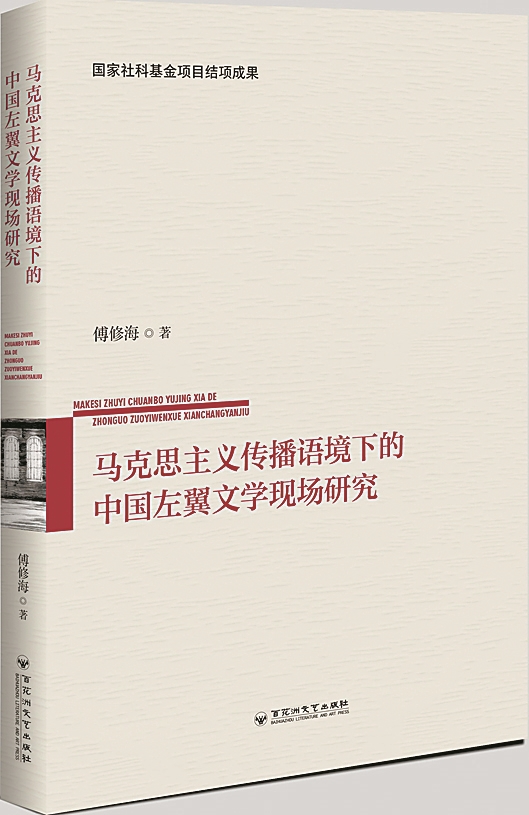
|
|
|
□林岗 对未被关注细部的发掘 中国现代文学史走过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历程,表征“革命文学”的左翼文学运动当然吸引研究者的关注。傅修海以瞿秋白文艺思想研究——《时代觅渡的丰富与痛苦》的博论初登学坛,十数年来,一直致力于左翼文学运动史研究。虽然间中开辟其他方向,但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擅长,故不时有新见发布。2015年他出版了《瞿秋白与左翼文学的中国化进程》,时隔六年再推出大著《马克思主义传播语境下的中国左翼文学现场研究》。 作为学人,当然期许自己能有石破天惊的创获,但此事谈何容易。不仅有关禀赋学养,更兼神秘的因缘时运亦为攸关。正如汉高祖既有“大丈夫当如此也”的由衷羡叹,如若不生于秦末群雄并起之时,则必然空有一腔热血。或嫌拟于不伦,然而王国维意义上的“成大事业、大学问”,必有非人力可致的因素,则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多年前读过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他以为科学发现的逻辑表明,科学发现是以一种模式取代另一种模式的方式前行的。新模式站稳脚跟之后将支配一段长时期。这段时期的科学发现,不表现为建构新模式,而是表现为沿着站稳脚跟的模式作伸延性的探讨,累积小创获小发现。当既有模式不能解释越积越多的小创获小发现,形成越来越多异常现象之际,新模式建构的时机就趋于成熟。这个道理其实同哲学讲事物变迁的量变质变的道理有异曲同工之妙。科学探索虽然不能等同于人文研究,但既然同为对真义的探究和发现,其中必有相似之处。例如生当社会格局和研究模式大定之世,再冥思苦想建立大体系发明大学说,无论你如何“望尽天涯路”,亦必将落入好高骛远的套路,必将劳而无功。反不如脚踏实地,从细处入手,积少成多,真义的发现亦尽在其中。 傅修海的这本大作,与既有的左翼文学运动研究不是大框架的不同,而是对前人未曾注意或关注不够之处的细部发掘。他十分机智地把文章做在“现场”,以左翼文学运动的“现场”研究为自己的特色。 将已见史料从纷繁中突显 以我的浅见,所谓“现场”就是构成文学事件的各种关系和细节。把尘封而混淆的关系梳理清晰,把当年的细节还原出来,事件的性质自然就活泼泼地呈现。“现场”既是傅修海大作观察左翼文学的视点,也是全书通贯性的线索。各章区分为“发生现场”、“创作现场”、“批评现场”、“传播现场”和“活动现场”。这些区分有些是含义相近的,但分别法无非就是方便的法门,故无需深究。 令我感兴趣读来有收获的,还是那些细部史实的还原和文本细读而获得的发现。如第三章有一节专门讨论《百合花》的意义。茹志鹃的小说当然很难简单地归入“左翼”了事,但无疑它是现代左翼文学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伸延和发展,因此它的叙事有一个傅修海称之为“当代演绎和变迁”的问题。他从茅盾的议论开始,梳理了60年来的评论,认为批评依然还没有说清楚它有什么好。这是因为前人未能发现文本的“表面”和“内在”的错位与统一。 他的结论我以为是富有启发性的:“《百合花》在文本的表面上是结构军民关系的故事,内在感情上则在诉说着军民之间朦胧美好的情愫。表里的错位和有机统一,使得《百合花》既可以叙写好政治统战性质的军民关系,又能保有左翼小说光荣的抒情传统,所谓合则双美。”傅修海的看法准确定位了这篇影响很大的短篇在当代小说史上的位置。 现代文学史去今不算远,史料辑录相对较为周全,未见史料的发现不容易。但有时候将已见史料从纷繁中突显出来还是很有意义的。第三章讨论“传播现场”,就《海上述林》的出版,鲁迅送书延安一事,傅修海的大作几乎将有关史料全数网罗。一旦如此呈现,它们在现代文艺思想史上的意义就显得不同凡响:一条从《海上述林》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线索就变得很清晰。尽管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和相关性尚待厘定,但却已经提示了学问探讨更进一步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