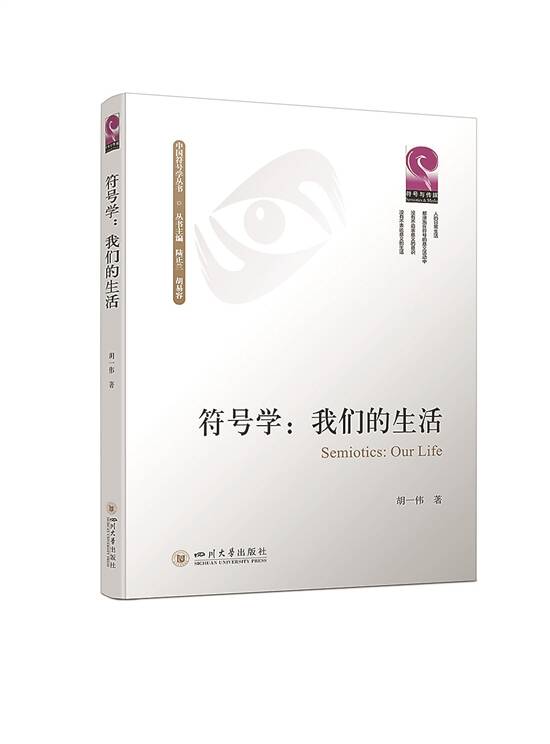
|
|
|
□赵毅衡 近年来,学问家开始注意向普通人传递知识,谓之普及。不过普通人不喜欢读太费脑子的书,要转换渠道。所以电视大学、网络讲课、老年大学、亲子教育等雨后春笋般涌现;另一种办法是出书“趣味化”,不是七零八碎的《十万个为什么》,而是把系统的专业课程讲得深入浅出。 这个潮流可能是日本人领的头,他们什么东西都能画成漫画;新世纪初,美国开始出现《傻瓜书》,开始好像是严肃题目,什么《给傻瓜看的尼采》《给傻瓜看的弗洛伊德》等,我读过,比原作更难懂,不知道好在哪里。此后就改变了路子,主题大多集中在电脑软件、电子产品中出现任何一个新东西,马上有一本《傻瓜书》;最近似乎走向形而下,出了《傻瓜学冰壶》《傻瓜学做菜》《傻瓜学化妆》,诸如此类。 十年前这些书大量译成中文出版,后来就发现不必了,我们的教育家自己能做,而且做得更好,因为我们的傻瓜比他们的傻瓜聪明。于是有各种“阿呆”“阿瓜”“阿衰”,只是题材内容多为少儿设置。 另一个系列来自学问家,而且刚出现:《趣味符号学》是鄙人所做,2016年出版;傅修延教授的《趣味叙述学》正在印刷机上装订,令人期待;胡易容教授正在写《趣味传播学》,等得让人头白。现在出现在面前的这本《符号学:我们的生活》,是南昌大学教授胡一伟所著,是一本非常特殊的学问普及化著作。它与先前的各种“趣味”系列,有什么不同呢? 最大的不同,是此书的对象:不是自称傻瓜的老先生,而是还在求知与求职的年轻人。这点非常重要,因为这个时代的年轻人不是傻瓜,而是心灵百窍、聪敏绝顶的未来世界的主人。我是老朽之人,因为是教书匠,不得不经常面对年轻人。每次遇到年轻人,心里紧张:闲说上两句,我知识浅薄,手脚笨拙,满耳新名词,一说三不知。在知识上、技能上、关心面上差异太大,知识代沟越来越宽。幸好是我在讲台上,他们在课座上,我可以捡我懂的陈旧知识讲,我知道我应该多联系他们的新世界新事物,但是要冒充年轻,力不从心。这就是胡一伟这本书最大的成绩:她自己是年轻人,她不用冒充年轻人,不用“联系”年轻人,她用的,就是他们的语言。 符号学这门学问,实际上很明白,符号学研究的是“意义的形式”。一般人觉得太深奥,因为对此形式,理论上只能找出抽象的规律。但是意义却是我们的生活浸泡于其中的东西,我们就像鱼一样生活在符号的海洋中,一口口吞下各种携带意义的符号,才能呼吸,才能生活。因此,符号学虽难,讲起来特别方便,随手可以就地举出许多例子加以说明。问题在于这些例子是否生动有趣。我讲课时也举例,只是例子太老一些:贾宝玉的玉,林黛玉的泪;阿Q的辫子,高老先生的长袍;孟子或王阳明如何说,柏拉图或尼采如何讲。我自己也觉得语言无味面目可憎,把学生都带老了。 看了胡一伟的《我们的生活》,才豁然开朗:符号学还能如此讲:各种“套路”(整蛊、撩人、酸醋);各种“尬”(“尬舞”“尬聊”“尬酒”“尬C位”);符号学论辩上最纠缠的“镜像”问题,被转化为现实生活中的“照骗”“海马体”;符号学理论上让人糊涂的“片面性原理”,被幽默成年轻人更担心的减肥、美容、美甲。符号的演化象征地发展,变成了各种地方戏的昨日与今日。 这才是年轻人的符号学,面对满堂年轻的眼睛,与其声嘶力竭地说符号学重要,不如“撩”一句:你知道符号学能帮你进行“身体管理”吗?与其列举各种哲人的思考,不如轻声说一句:各种让人馋涎欲滴的菜名,原来是符号的无限衍义;与其黑板敲得震天响,不如说一句“土味情话梗”,才鞭辟入里。 那么为什么我做不到,而胡一伟轻而易举呢?因为这不是“我的生活”,而是“他们的生活”。我们作为人类,生活固然浸泡在符号意义中,但是生活与生活不一样。胡一伟与她的学生生活在同一水域,她们在类似的符号大海中畅游,吞吐同样成分的意义形式。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是一本年轻教师写给年轻人看的书:用同样时尚的语汇,讲同样有趣的故事,虽然背后可能讲出了这门学问中共同的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