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周文翰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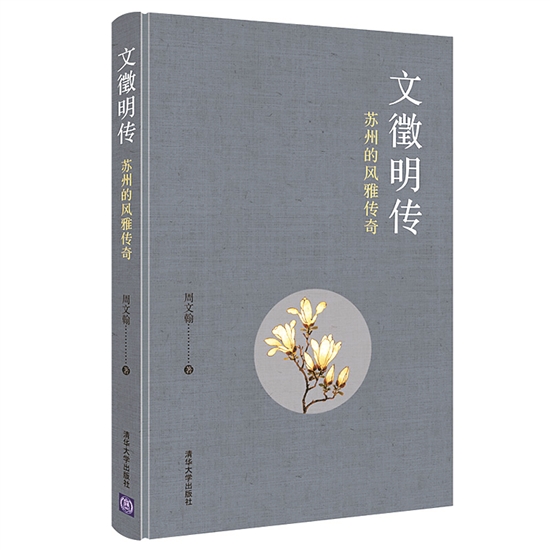
|
|
|

|
|
|
文/羊城晚报记者 吴小攀 古代文化名人传记一直备受热捧,一些不太受重视或有“歧见”的书画艺术大家的传记近些年来也开始走红,作家、艺术评论家周文翰一直潜心于相关创作,继出版文徵明、赵孟頫传记后,黄公望、倪瓒、王羲之、苏轼、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的传记也将陆续推出。关于古代艺术家传记的写作有何体会?对当下的美术创作有何观感?日前周文翰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 文化上的“思乡病”促成写作 羊城晚报:为什么会选择这些古代的艺术家写传记? 周文翰:二十年前我大学毕业,最开始关注的是当代艺术和创意文化。2002到2008年我在北京当记者,主要报道当代艺术和文化,之后辞职去印度、西班牙等地旅行,旅行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对古典艺术、对日常生活所见的动植物这些主题产生浓厚兴趣,兴趣转移到艺术史、博物学上。 可能是在异国他乡有了文化上的“思乡病”,也可能是对当代艺术的“转瞬即逝”“好奇求异”感到迷茫,我反而开始对似乎是“陈迹”的古典文化有了浓厚的兴趣,从那时候起开始写作《中国艺术收藏史》。在写作中发现,赵孟頫、文徵明、王羲之等虽然名字为众人所知,但是大家对他们的人生、性情并不了解,他们的形象是模模糊糊的,对今天的人来说,他们是“著名的空心人”。既然如此,我就决定自己来写他们,这一写就持续了十四年,对我来说,写作古代艺术家传记的最大动力就是希望能让这些古人“活起来”。 羊城晚报:已经写了哪些人? 周文翰:我喜欢同时写好几部书稿,有的写得快些,有的写得慢些,也有的写着写着就“烂尾”了,第一批写的是文徵明、赵孟頫、苏轼三个人,前两本已经出版,后一本《孤星之旅:苏东坡传》年底应该能出来。第二批写的是“扬州八怪”、王羲之,前者是因为我对扬州一直有些迷恋,想从扬州的城市变迁角度写扬州八怪,后者是因为写了前面三位书画家,有一段时间对书法突然很感兴趣,就追溯源头,写起了王羲之,明年应该能出来。还有几本都已写完初稿但还想打磨一下,有黄公望、倪瓒,李白、杜甫、白居易,基本上都是在写一个人的过程中,突然因为某个细节、某句话对另一个人产生了兴趣,转而就写其他人,如此就越写越多。 羊城晚报:这些人有什么共同点? 周文翰:研究和写作这些艺术家、文人的传记之后,最大的感想是“龙有龙道,蛇有蛇道”,刺猬、狐狸各有归宿,每个艺术家的天赋、性格、背景都不同,他们有各自的成长之旅,成名之路。总的来说,这些艺术家绝大多数都是士人、官员,这是他们的核心身份,书法、 绘画是他们的“业余才艺”。而吴道子、黄公望两个人身份特殊点,吴道子是画师出身,最初的身份是比较低微的,黄公望则是吏员、道士,打交道的也主要是低层人士。 最困难的是“带着同感理解古人” 羊城晚报:写古人传记要达到怎样的效果,有没有给自己设定目标? 周文翰:我写传记是希望写出活的人,同时写出真实的时代氛围、文化生态,我自己觉得在史料辨析、整体信息的传达上应该都达标了,但是在古代人物传记的“体式”或者说写作技巧方面还在持续探索。比如,第一本《文徵明传:苏州的风雅传奇》努力想要挣脱“评传体”,但难免还保留了许多“评论腔”;第二本《不浪漫:赵孟頫传》的评论腔就少了很多,基本是按照传主的视觉、听觉展开叙述,在摸索如何处理史实方面的“硬信息”和个人感知的经验“软信息”的比率,即将要出的苏东坡的传记可能会更加平衡。 羊城晚报:写古人最困难的是什么?如何把握虚构和非虚构的分寸? 周文翰:最困难的是“带着同感理解古人”,即所谓“理解之同情”吧。今天的人因为看影视剧比较多,影视剧是快节奏、强冲突的模式,而实际上古代人对时间的感知、对空间的感知、礼俗细节等等都与当代人有巨大的差别,比如古代人骑马、乘船,一天经常只能走四五十里,而今天的人乘坐飞机、高铁、汽车,一天能走上千公里。我在写作中是比较强调“视觉性”和“空间感”的,目前写的艺术家传记都是严格根据史料来写的,没有任何虚构的成分。 说到虚构,《吴道子传》这本书最让我为难,因为唐人关于吴道子的记述总共就一两千字,而且几乎都是关于他在寺观的画作的简略记述,因此想写出他的“严肃传记”是不可能的,要写他的传记的话只能加入“虚构”才能勉强凑出他的“人生”及其画面感,可是,如何“虚构”?如何把史料、信息与虚构结合?这让我挺犹豫的,写了近二十万字的草稿但是一直拖延、犹豫,中间停下来又去写了李白、杜甫,因为他们三人生活在同一个时代,而且李白和吴道子都是翰林待诏,肯定在办公的院子、酒宴上寒暄过。 中国艺术“地位”随中国发展“水涨船高” 羊城晚报:近些年来有些艺术史家如高居翰、巫鸿等人从海外的视角,撰写了一些有关中国艺术史著作,您如何评价? 周文翰:他们因为是学者,基本是按照学术规范来写作的,许多具体的观点挺有意思和启发。我不认为西方人解读中国艺术就会“隔”,因为中国古代文化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了“专门知识”,无论中国人、外国人,想要严肃研究古代艺术都需要长期的学习和积累,都要慢慢摸索自己的研究方法和写作方法,所以好的研究者肯定是“争奇斗艳”,无所谓“隔”不“隔”,最多是理解不同而已。 羊城晚报:包括毕加索、塞尚、凡·高、高更等人多少都受到中国传统美术的影响,但之前似乎并没有引起足够关注,是不是需要更充分地评价中国美术在世界美术史中的地位? 周文翰:在我看来,这很大程度上不仅仅与作家、学者的写作、倡导有关,其实与中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有关,比如现在很多欧美艺术家愿意承认中国经历、中国艺术对他们的刺激或者影响,这是因为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文化的影响自然就大了许多。随着国内大学的扩张和研究竞争的激烈化,对中国艺术的研究还处于增加的阶段,我相信如果持续下去,包括与海外的出版界、新媒体增加交流的话,会促进外界或者说外国人对中国艺术的理解,如此中国艺术的“地位”自然会“水涨船高”,你本身成为一个强势的存在,自然会吸引别人的关注、研究、传播。 艺术价值“共识”随着时代演变 羊城晚报:从古代艺术家的生平里,您认为最值得当下艺术家借鉴的是什么? 周文翰:古代和现代最大的不同是,书法、绘画这类才艺是古代士人的业余技能,他们的主业其实是当官,其次是诗文,书法、绘画是排在后面的;不像现在,书法家、画家都是光明正大的职业,而且当代艺术家可以利用公共博物馆、互联网开放资源学习甚至开展商业,可以尝试的艺术风格、商业渠道都比古代艺术家丰富得多,所以我觉得当代艺术家没什么可羡慕古代的。能借鉴的,可能是他们的一些图式、理论之类,但是在人生方面其实没有什么可比性。赵孟頫、文徵明都是谨小慎微、温和平润之人,苏轼既能写文章,也会讲段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路,苦难能出诗人,幸福也能出诗人,不是绝对的。 羊城晚报:您认为当下艺术家在继承本土传统与向西方学习之间,哪个更重要? 周文翰:我觉得21世纪的艺术家的基本境况是:一个人面对着数千年来的、全球的所有视觉文化遗产和图像,眼花缭乱,这时候很难说是面向本土或西方学习什么,因为可供学习的知识、图像实在太多太丰富了,最多挑选几个细小的方向深入探究,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细分的爱好、方向,实际上一个人只能向几个古人学习、致敬,类似一个个的小社群,不是以东西方划分,而是以更细微的趣味划分。在此中“平衡”对当代人来说难度太高,还不如痴迷一两样东西好。 羊城晚报:在这样一个全民都画的时代,如何判断一幅画的艺术价值? 周文翰:这是我在《中国艺术收藏史》中研究的问题,简单地说,就是一幅画的艺术价值是各种利益、观念的互动形成的“共识”,具体每一件作品的“共识”都有差别,有的市场价格的高低是主因,有的皇家收藏履历是主因,有的创作者自带“名人光环”是主因,各不相同,很难给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答案,而且这种“共识”也会随着时代演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