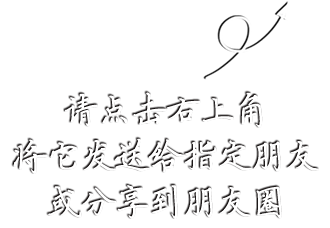□彭典也
“他/她到底在想什么呢?”
与这句话相关联的我的回忆,似乎都笼着一层发霉的蛋糕皮。
首先出现在那处的是路灯。不是舞台上的那一盏,而是立在崖边,被夏夜的飞虫环绕,向着其下层区域毫无保留地散发光芒的“那盏路灯”。
接着,两个学生沿着旋转的石阶下来了。还有几分钟下堂晚修;不急,我们才刚下来,应该还能再遛一会儿。其中一人频频望向阶梯旁的暗影(其上有一块凸出的甲板,导致路灯光只能到达荫蔽边缘);另一人只用余光悄悄扫视那片可疑的黑暗。有一刻,两人都没有作声;但紧接着,对话重又开始。他们兜了一圈,旋上楼梯离开了。
随脚步声远去,寂静又迈着大步前来。路灯光下,一切是如此平和。可那片暗影仍在那里,它是画面里唯一的不确定因素,像凭空出现的黑盒,每个缝隙都往外渗出丝丝冷意。
是时候弄清那里究竟有什么了。正好,周围没有别人,可以尽情冒险,大胆地上前观察;或者不必承担过多风险,只需要走下几个台阶,遇到危险也方便逃走。
勇气把路灯稍稍擦亮了点,此时可以看见暗影中有一簇白光,稍加辨认可以确定此白光来源于一部电子书,停在阿图罗·贝拉诺与伊内基决斗时的段落。“我又想,这一场景不过是我们荒谬生活必然的逻辑结果。”《荒野侦探》中的词句,文段,白光,以及柔软的外壳,都溶解在弥散的黑盒里。
周围的气流轻微地搅动。这样无风的夜里,空气怎么会无端地扰动呢?察觉到端倪,那就睁大眼睛去看,相信一定能有新发现……
当这个身影出现在视野中时,这些问题都迎刃而解了。在灯光和暗影的交界,在最显眼却是最不易发现的边界,原来站着一个人。我们起先完全没有发现她,但这并不是我们的过错。她的一半嵌合在灯光里,另一半拖拽在暗影中,被浇筑成无边夏夜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我们原先以为是飞虫的振翅声,原来是她正在朗读段落;我们原先以为是黑盒边缘的部分,原来是她的发丝在悄悄收束周边的光线,准备把它们关进盒子里,再以高价成交。她孑立在此处,把周身的环境都模糊了,好像来自她手中的文段,而非这个不容置疑的世界。
比起先前问题的解决,她反倒带来了更多问题:你是谁?你为什么孤身一人?你能不能转过身、让我们看看你的正面?你为什么在这里读书?你是不是在惺惺作态?你是不是期待有人来找到你?那两个学生过来的时候,你看见他们了吗?你被他们看见了吗?你感到痛苦吗?你觉得夜色美好吗?你觉得你毁了如此美好的夜色吗?你真的存在于此处吗?你为什么如此安静,如此游离,以至于我们的视线都透过了你,看到了砖缝里的杂草,看到了蚂蚁的尸体,唯独注意不到你就在此处,孤身一人湮没在光与影里,直到从路灯下消失了呢?
事已至此,仍有不合理之处。世上真有这样的人,如此游离以至从环境中近乎完全地淡出吗?而这样的她却出现在我们面前,又能怎么予以解释?
事态陷入僵局。在这个当口,所有的人都哑口无言,都在等身边的人先开口说些什么。什么都好,只是别让这恼人的死寂再持续下去。
终于,我们中的一个人发话了。她的嗓音就像黏合在一起的两个齿轮,先由一个小的转动起来,再带动大齿轮慢悠悠地旋转。这时如果有人望向夜空,就会发现所有人头顶都悬挂着同样一柄由无数松散的星辰组成的巨剑。但是大家的注意力都不由得聚焦在了说话的人身上,就算剑掉下来,切开我们的脑袋,也无人能反应得过来逃脱。
我们心想:我们就是她啊。因为她说道:我知道了,我就是她啊。我就是那个站在金色与黑色之间的人,捧着书的是我,朗读决斗场景的是我,溶解在夏夜里的是我,我孤独一人,忽略了身边的一切,以至于一切也忽略了我,让我变得近乎不存在了。
我站在路灯下,与自己面面相觑。忽然间,我们所有人同时抬起头,望向夜空。那柄剑不知何时挣脱了镣铐,正向着地面飞速坠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