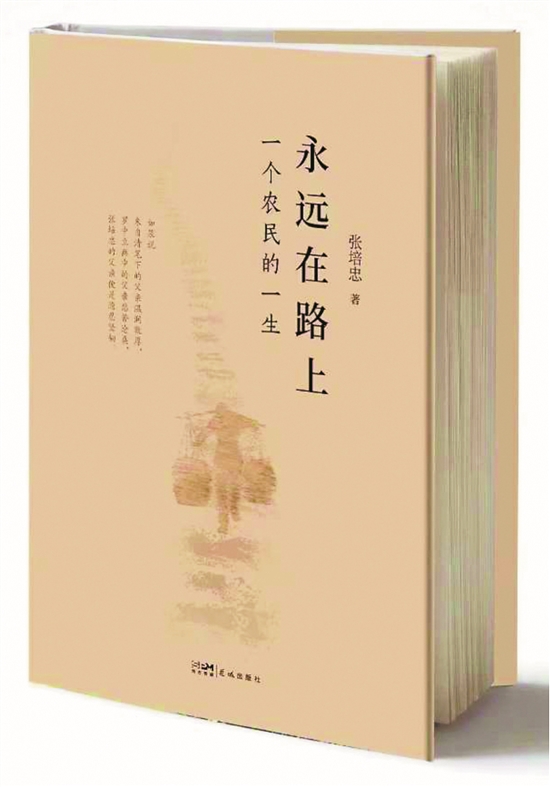
|
|
|
□张培忠 一本别样非虚构的书的由来 今年是父亲去世40周年。父亲远行时,得年50,我则是一个懵懂的17岁少年。岁月倥偬,惊心动魄。父亲断断续续只读到小学四年级,文化不高,但他始终志行高洁,容止可法,是一个朴实勤劳的农民和可亲可敬的父亲。 父亲去世30年时,我写了中篇纪实作品《永远在路上》,探寻父亲、追怀父亲、感恩父亲。这篇近四万字的长文,发表在《中国作家》杂志2012年第7期,是我酝酿时间最长、素材积累最充分、收获最多感动的一篇非虚构文字。父亲去世后,我在最初的中师日记里就不断记录梦境中出现的父亲形象:有时是躺在医院里那苍白的脸孔,有时是肩着沉重的犁铧那佝偻的背影,有时是踯躅在山间小道寻找前行的方向……常常一觉醒来,一片虚空,泪流满面。及至农村学校任教后再到大学就读,创作的短篇小说《野渡无人》《魔火》,当中都曲折地寄寓着父亲的形象。 人之所以为人,必得心有所主、情有所归,其至道即在于孝,孝为第一要义。中国几千年历史,强调“圣朝以孝治天下”,没有对父母的孝,就不会有对国家的忠。由孝到忠,移忠作孝,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不可或缺,交相辉映。因此,在我看来,一个知识人,一个写作者,其最大的孝道,就是把父辈的历史搞清楚,把父辈的人生写出来,追本溯源,继志述事。 为写好纪念父亲的文章,我请母亲来做口述史。父亲走得早,人生履历留下许多空白。所幸母亲有着极好的记忆力和极佳的表达力,她虽一字不识,却通达情理,洞明世事,人间冷暖,了然于胸,每次讲述父亲的故事,她都不疾不徐,娓娓道来,前因后果,来龙去脉,情态毕现。为了更全面地获取父亲的生平资料,我还借回乡探亲之机,走访了父亲的少年好友张志勇和青年同伴张愈成,在他们的深情回忆中,还原和显影了父亲的点点滴滴。在一次又一次的讲述中,父亲的历史廓清了,父亲的形象饱满了。 仅有口述,仍显空疏。为真切感知父亲在艰难环境中的坚韧精神,十年前的清明节,我专程从广州回到老家,与哥哥一起沿着父亲当年“走山内”“走凤凰”的足迹逐一寻访,同时也为《中国作家》即将刊发《永远在路上》选配图片。那天上午,我们先到胜利水库主坝踏勘,苍茫的山野,寂静的荒径,无声地诉说着曾经的艰辛。这是父亲跋涉过大赤岭、枫树脚岭后走向山内的必经之地。哥哥说,父亲当年曾在这里摔了一跤,那一跤,使壮年的父亲感受到生命的寒意。然后到坪石,饶平通往大埔境内第一站,寻访到父亲当年经常落脚和晚上歇息借宿的房东陈国材伯伯,他已87岁高龄,却精神健旺,双脚因前两年摔断,行路时需借助两张椅子帮助移动。听说来意,他恍然大悟,三十多年了,仍对父亲印象深刻,还记得我的伯伯张春光,并说曾到过我家做客。他的二儿子则对父亲直锯劳作记忆犹新,还示范当年情形。正谈话间,陈国材伯伯的弟妇走了进来,听说我们是德建哥的儿子,她说当年在上伦墩锯柴时,父亲他们就在她家里做饭一起吃,彼此就像一家人。老阿姨一边走一边不停地叫着“德建哥,德建哥”,那亲切又陌生的声音,听得我眼睛湿润,好几次差点流出眼泪。她还自告奋勇带我们到上伦墩锯柴时父亲曾住过的房子,可惜已是断垣残壁。 离开坪石和上伦墩,一路上山下山,来到桃源镇,一个山中的陶瓷城,那是父亲“走山内”的终点站。在一个大排档吃午饭,饭后再往高陂镇,站在堤岸上,现场体验了韩江水的浩瀚壮阔和高陂路的迂回繁复。从高陂镇又回到桃源镇,找到在陈厝楼当年父亲经常借宿的房东陈华昆伯伯。老人家年届80,也是父亲的老朋友,他感叹当年父亲挑猪仔来卖的艰难,还带我们凭吊了已倒塌的老屋。临行与陈华昆伯伯握别,离情依依、不胜感慨。父亲那一代农民终成绝响,但他们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代农民,特别是有着从事“绣花农业”之称的潮汕农民,他们的欢欣苦累、生存状况、喜怒哀乐岂能随之湮灭?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身处举全社会之力推进乡村振兴的现实语境中、集全国作家之笔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的时代洪流中,对于父亲和他的底层生活、乡村世界、精神肖像,我想应该有文字记录,为时代作证,毕竟历史不能忘记,更不能割断,而每个生命都是唯一的、独特的,无法逆转、不可复制的。于是,有了这本书,一本别样的非虚构的书。 全球视野下的非虚构写作 这些年,“非虚构”引起文学界高度关注。根据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徐剑先生在《报告文学、非虚构的理性辨识与文学分合》一文的研究:“最早将‘非虚构’一词引入中国文坛的,是我的老师周政保先生。20世纪90年代后期,周政保先生出版了一部学术大作《非虚构叙述形态》,第一次对非虚构的文学叙事方式进行理论性的阐述。”天下事无巧不成书,周政保先生也是“我的老师”,徐剑会长讲到的那本著作,周政保老师在2000年元月就签名送过给我,当年我还根据他书中的提示找到了美国作家杜鲁门·卡波特那部非虚构作品的开山之作《冷血》进行比较研究。而在此前的1990年,我正依违于业余从事理论研究还是从事文学创作而纠结不已时,周政保老师从天山北麓及时来信指点迷津说,一个人能做好一桩事就算是很好了:譬如,或理论研究,或某一门类的创作。摊子太大,总不易深入。于是,我选择了非虚构文学创作,一直坚持到现在。 做这样的选择,有兼顾工作的考虑。其时,我正在省教育厅由秦牧先生创办并担任第一任主编的教育杂志从事编辑工作,因为这个缘故,我多次拜访请教先生,先生还亲切地称我们是“先后同事”;与此同时,我还参与编辑另一本月发近400万册的少儿杂志,主持“名人的少年时代”栏目,登门拜访并约请刘绍棠、张洁、李国文等老师撰稿。这些工作都与非虚构、与文学密切相关。 当然,我选择非虚构着力,更多的是注目于全球视野下读书界、文学界的走势。美国《纽约时报》知名报人詹姆斯·赖斯顿指出:“十九世纪是小说家的时代。二十世纪是新闻工作者的时代。”早在1975年美国出版的大约30000种新书中,只有2407种是小说。《纽约时报》书评版编辑每年推荐100本值得关注的作品,发布年度10本好书,其中非虚构都占一半以上,可见今天的美国人喜欢读真人真事仍胜于读小说。国内的读书界和文学界也有类似的趋势。事实上,追索真相是人类的天性,更是人类的权利。而在21世纪,在互联网时代,仅靠单一的方式来呈现真相,显然难以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因此,本书用多维的视角、立体的层面,通过报告文学、书信、日记、口述历史、文学评论、现场图片、笔记图表、实物展示等进行聚焦、透视,全方位展示一个中国农民的一生。 一位知名非虚构作家曾深刻写道:“研究中国问题,如果没有底层、农村、贫困的参照系,没有这些层面——一个涉及十亿左右人口的层面的深切观察和体验,很难把握中国社会的走向。”如果说,传统报告文学侧重于宏观叙事,那么,非虚构文学则侧重于微观叙事。本书所呈现的是半个世纪前后的中国农村,特别是一个中国农民在山村、在底层,为了躲避贫困、解决温饱而奔波不息、艰难前行的生活情状,以及此前此后所经历的沧桑巨变。这是一个农民的人生档案,是一个时代的忠实记录,也是一个民族的共同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