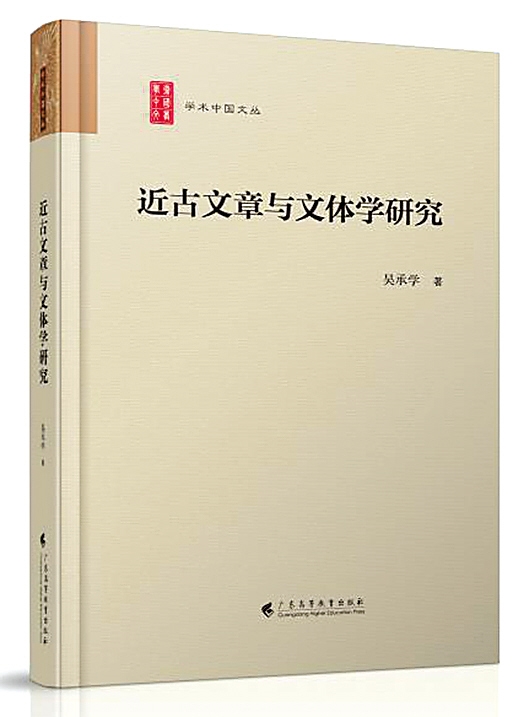
|
|
|
□吴承学 四十载聚焦文章学与文体学 本书是我在近古文章与文体学研究方面的部分成果。所谓“近古”,或称“近世”,指宋代以降至现代之前。学术界对于中国“近世”的政治、文化的特点,多有论述。本书比较集中地讨论近古的文章学与文体学。 中国文体学盛于南朝,近古又是一次极盛的时期,其研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远迈前代。“辨体”之风,自宋代而来,至明清而集其大成。对文章体制规范及其源流正变的探讨是近古文学批评的核心议题之一。宋代以后,古文取代了骈文的统治地位,文章学也随之发生重要转向:从魏晋南北朝的骈文文章学转而形成古文文章学。从骈文中心时代到古文中心时代,文章学的评价标准发生明显的变化。近古以来的中国文体学、文章学对于现代中国人的影响更大,更为直接。本书从一些比较特殊、少人注意的理论形态切入研究中国古代的文体学与文章学。比如,近古以来的文章总集与文章学、文体学的新形态,评点之学的渊源流变,目录学与文学批评,类书与文学批评,近古以来文章学与文体学新形态,以及相关的经典学问题。 书中所收的论文,最早写于1982-1984年期间,是我的硕士论文的一部分,最晚则是刊于《学术研究》2020年第六期的文章。本书写作时间的跨度差不多贯穿了我已有的学术生涯。 回首匆匆,许多经眼事物,转瞬之间,已成遥远的过去。 从蹒跚学步到独立放飞 上个世纪50年代,我出生于潮州一个教师家庭。我的祖父长期在海外当私塾先生,“文革”中回国。父亲解放前在重庆、上海从事考古、电影等文化工作,解放后回到潮州任中学语文教师。从小学开始,我就遇到“文革”,一夜之间变成“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幸好,温馨的家庭、丰富的藏书给我以最大的慰藉与保护,善良而有主见的母亲总是勉励和支持孩子们读书向上。对我来说,这种印象是刻骨铭心的。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所谓的学习,完全是出于纯粹的兴趣,没有任何功利目的,当然也相当粗浅和零碎。但这些无心插柳之举,居然为后来的专业研究打下某些终生难忘的“童子功”。更重要的是,我从小就明白自己的喜爱与特长,多年以后,以研究中国文化为志业便自然而然成了我的不二选择。 “文革”结束,我成为恢复高考制度后第一批大学生,后来又继续攻读硕士、博士,圆了少年时代做读书人的梦想。改革开放的时代,进入学术领域。那是一个令人激动的年代,在前辈学者的引领下,我们很快便完成了从蹒跚学步到独立放飞的进程。 站在学术发展史的角度看,任何一代学者,都是承前启后的。承前,决定了一代学者的素质与水平;启后,标志着一代学者的地位与影响。如何评价我们这一代学者,这有待来哲。 固执传统“发现”历史 一代学者所处的大环境相似,所以有一定共通之处;一代学者的个性与兴趣不同,所以又各有差异。在这一代人中,我就是一名教师和学者而已。曾有学生问我,在八九十年代的学者中,我个人的治学特点是什么。答曰:固执传统。“固执”是研究态度,“传统”是研究领域。 我的主要工作,是赓续和阐释近代以来受外来学术影响而中断的传统学术,一直集中在传统领域里的传统话题:中国诗文批评、文章学与文体学等,意在立足本土文化,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回到中国本土理论传统与古代文章文体语境来“发现”中国文学自身的历史,重现中国本土文学与理论的特殊光辉。传统的人文学,主要是学术的积累与阐释,有些研究对象是亘古话题,并非无中生有的“创新”。要“开拓学术之区宇”,必先“承继先哲将坠之业”。不同时代的接受者由于视野不同,对传统话题有新的理解与阐释,用自己的思想与情怀和古人对话,从而获得渐次的推进。 我总认为,学术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提出有学术史意义的问题并期待解决,而不是为了填补空白。填补空白并不一定有意义,并非所有空白都需要学者去填补。文化创新的同时,需要文化保护。某些传统是需要有人保守,有人呵护的,就像茫茫大漠中的敦煌石窟需要一代代的守护者。 古人说,勤能补拙,其实,恒亦补拙。我别无所长,若有的话,便是固执。四十年来,固执于传统领域的研究。日于是,继之以夜;月于是,继之以年。坚守寂寞,远离喧嚣,以冀盈科而进,聚沙而成塔。 从事教职出于快乐选择 世上有许多伟大、荣耀的工作,我对之虽然佩服,但不羡慕。正如古人所说的,“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我深爱自己的工作和职业。我并不认为它比其他职业更为神圣、崇高,只是最适合我罢了。 小时曾读柳宗元《捕蛇者说》,印象极为深刻。永州有三代从事捕蛇者,虽然“吾祖死于是,吾父死于是,今吾嗣为之十二年,几死者数矣。”但在赋敛制度下,捕蛇这种貌似最危险的职业,却能得到相对的安全与自由。不知为什么,我读这篇文章,常常会产生一种完全相反的怪诞联想。我们家世代以教师为业,我的爷爷是教师,我的父亲是教师,我十多岁就开始当教师,教过小学、中学、大学,至今已四十多年。捕蛇者世代从事此业,是由于一种无奈的消极选择,而我则是出于积极的快乐选择。 虽然,教师的政治与经济地位曾非常低下,现在当然不同了,但毕竟不是有权势或可发财的职业。不过,我真心喜欢教师与学者这个宁静而干净的职业,这纯粹是一种个人的爱好。说得俗一点,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说得雅一点,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陶渊明《杂诗》云:“昔闻长者言,掩耳每不喜。奈何五十年,忽已亲此事。”长者之言,往往老生常谈,宜为年轻人所不喜;而一旦亲涉此境,枨触遂多。我以前读此诗,领略尚浅,如今已成“长者”,读之则相视一笑,莫逆于心矣。 以上詹詹之语,乃一时之感触耳,不知后生闻之掩耳不喜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