囗欧雪华 在我家村口,那青石砌成的老井旁,有一棵老槐树。 老槐树的花瓣如雪般覆盖枝头,在井边绽放,又是一季槐花的飘香,闻着那花蕊,夏天,踏着季节的脚步如期而至,我们的夏日仪式便从槐枝上第一簇白花开始了。 当晨光还未切开薄雾,妹妹就拽着我的衣角来到井旁打水,因为那时候我们村还没有自来水,家家户户都要去打井水,所以爸妈给我的任务就是每日清晨去挑水回来,当木桶打水的碰撞声与鸟鸣交织成村里的晨曲时,也唤醒了沉睡的露珠。妹妹的小辫子沾着几片槐叶说:“姐,今天的花比昨天多。”朝她手指望去,槐花正从树叶的墨绿里渗出来,团团簇簇压弯了枝条。井绳绞着辘轳吱呀转动,水桶沉入井底时,我们会试探着把头探进井底传来自己的嗓音:“数到二十就开花啦”,那个回音使枯燥繁重的挑水任务在花香中变成清凉的期待。 挑完水,趁母亲在灶间熬粥的工夫,我们会互扶着顽皮地攀上龟裂的树皮,指尖刚触到花穗,露水就簌簌落进衣领。妹妹在树下张开围裙,接住那些带着晨露的花。最嫩的蕊心泛着鹅黄,我们像两个啄食的麻雀,一瓣瓣撕下蘸着井水的花来吃。“甜不甜?”她总这么问,井水刚从十丈深的岩层里醒来,裹着地脉的凉意蹿上脊背,把暑气劈成两半。槐花的蜜香在舌尖炸开时,我的齿间嚼着花瓣像含了碎玉。有时干脆摘下一串串洁白的槐花,泡在刚打上来的井水里,用搪瓷碗装着,看着花瓣在水中舒展,我们轮流把脸埋进粗瓷碗啜饮,感觉清凉中带着淡淡花香。蝉声很好听,不久肚子便咕咚咕咚地唱起歌来了,感觉好饿。这不,回去又挨了妈妈的一顿骂,她怕我们生吃,会吃坏肚子。可她哪知道那井水的清甜与槐花香绕过舌尖,成为我们对抗酷暑的秘密武器。 那天,烈日正烤得井台发烫。父亲发现我和妹妹生吃槐花和井水,他的烟袋锅敲在青石上迸出火星。“又喝生水!”我们贴着槐树罚站,树影里藏着昨日没吃完的花串。妹妹偷偷用脚趾勾过来,残花泡在午后积雨里,发酵出酒酿般的醇香。这味道后来总在梅雨季冒出来,混着井台青苔的腥气,而我们姐妹俩从未因生喝槐花泡井水而拉肚子。现在想来,应该是我们客家人自古讲究“应时而食”,槐花性凉,井水性寒,二者相配正是消暑良方。井水经过地层过滤,富含矿物质而洁净温和;槐花能清热解毒,却不会像冰镇饮料般刺激肠胃。我想这可能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朴素养生哲学。而我们明知父母禁止饮用生水,却仍沉醉于这冒险的甜蜜,每次偷喝都像一场小小的反叛。至此还对父母的关心有点内疚。 井水其实有微微的泥沙味。多年后我回到村口的老井,才发现那些清甜多半来自槐花。但那个夏天我们确实喝下了很多生井水。记得那天的雨,跟往常一样来得蹊跷,先是扬了三天槐花雪,门前的整个晒谷场都浸在淡紫色的光晕里。在晒谷场我们还听见花苞绽裂的脆响,像老祖母捻动佛珠时的咔嗒声。直到我们在晾晒的花毯里发现那几片紫瓣——薄如蝉翼的弧度上,还凝着雨水呢。晴后,我和妹妹会迫不及待地去拾起地上的槐花,放在我们的标本册,像被晚霞吻过的信笺,漂亮极了。 后来,那避暑的槐花井水的夏日印记在梦境与现实中反复浮现。我总梦见那个炎热的午后:“晒蔫的南瓜藤突然疯长,爬过土墙去够远处的山梁。”妹妹把槐花夹进字典扉页,油墨字迹便染出井水的虹彩。每当暴雨来临时,整个村庄在蒸汽里浮动,她踮脚把标本册举过头顶,像举着一盏不会熄灭的灯。 俗话说得好:“槐林五月荡琼花,郁郁芬芳去万家。”槐花盛开的季节里,蜜蜂嗡嗡,蝴蝶轻舞,空气中处处弥漫着槐花的味道。漫步在槐树下,一阵凉风吹来,熟悉的槐花香味扑面而来。在桃花梨花争奇斗艳之后,那星星点点的槐花,还在散发着一股沁人心脾的清香。 如今拧开水龙头就有自来水,却再难寻得那口老井的甘甜。村里的槐花早已褪成了月色。但每当我翻开旧书,总有几片花瓣从时光褶皱里飘出来,提醒我某些奇迹的确发生过——就像最贫瘠的土地,也能长出会飞的种子。偶尔想起,舌尖似乎还能回味那混合着泥土芬芳的清凉,那是记忆里最天然的空调,最本真的夏日味道。
-
即时新闻

槐井酿夏记
来源:羊城区域
2025年09月30日
版次:ZT16
栏目:
作者:欧雪华
分享到微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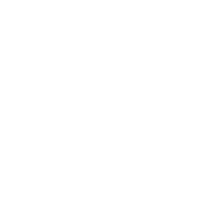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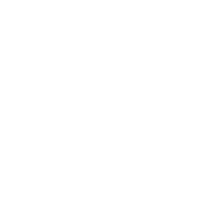
使用"扫一扫"即可将网页分享至朋友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