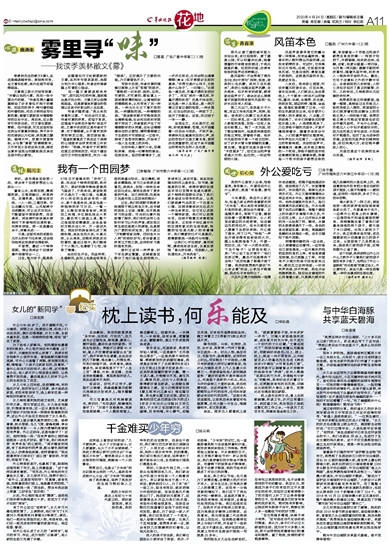|
|
自启蒙始,我受的教育便是“坐如钟、站如松、行如风”,但凡读书必正襟危坐,眼观鼻、鼻观心,腰杆笔挺,最讲究读书的姿势。可我生性顽皮,常挨不过课堂45分钟,趁人不注意便偷偷溜出去“放风”。倘不幸被先生逮着,实实在在的几下教鞭,落在掌心,打得生疼。可我仍照溜不误。依我看来,端坐着读书,其受罪程度不下于“人生三苦”:撑船、打铁、卖豆腐。古来圣贤映雪囊萤、悬梁刺股的劲儿,我实在是学不来的。 俗话说,好吃不过饺子,舒服不过躺着。我偏偏最喜仰面朝天地躺在沙发或床上,随手翻翻闲书。 可父母最是反对我躺着读书,常叨叨:“书没读好,眼睛倒先看坏了!”为图个耳根清净,我索性卷起被褥,一个人搬到阁楼上,靠在藤椅上,临窗而坐,一手捧书,一手持笔,每有会意,便圈圈点点。最惬意的,莫过于冬夜里拥衾夜读。 秋冬夜长,吃罢晚饭,我便早早钻入被窝,一边是窗外“北风卷地白草折”,一边是洗涤干净的枕套、棉被散发的淡淡暖阳清香,我便是这样啃下了比砖厚的《史记》《古文观止》及诸子百家系列……这类深奥难懂的国学古籍,需一文读几遍,方能精华尽览。秦汉风云、魏晋风流,远比今人的微信、微博要好看且耐读,让我顿生踌躇满志之感,至今仍能倒背如流《滕王阁序》《过秦论》等名篇华章。我也爱长篇文史巨牍,诸如王鼎钧的回忆录四部曲《昨天的云》《怒目少年》《关山夺路》《文学江湖》,于太平之世回顾历史,不见煽情,没有呐喊,平心静气,却触及灵魂。还有些书值得细细品味,魏文帝曹丕之《燕歌行》就让我百读不厌。 捧书而卧,与李、杜同饮,共苏、辛对座,我常常一气呵下数章,半日读完一本。时光人物,倏忽而过,书里书外,驰骋遐思,这样的枕上时光,何乐能及?个中滋味,大概只有林语堂大师可以感同身受。他亦认为蜷卧在床上乃人生最大乐事之一。我曾借鉴他老人家的躺读姿势:“最好的姿势不是平躺在床上,而是垫个柔软的大枕头,枕头与床约保持三十度的斜角,然后枕臂而卧。在这种姿势下,任何诗人都能写出不朽的佳作,任何科学家都会有划时代的发明。”这招令我受益匪浅,以致我后来坐着面对电脑屏幕,反而大脑一片空白,唯躺着码字,却文思泉涌。 其实,很多古人都喜枕上读书。“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汉赋大家扬雄居所孤寂,成年累月枕书为伴,终于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巨擘;“文章名冠天下”的欧阳醉翁更擅长见缝插针,用散碎时间读书:马上、厕上、枕上;就连一向不苟言笑,以冷峻面目示人的鲁迅先生也在《病后杂谈》中调侃“大可享生病之福”,原因即是可以躺着看点不劳精神的线装书来“养病”;受宋人蔡确“纸屏石枕竹方床,手倦抛书午梦长”的影响,我有时在炎炎暑日午后,还常跑到老宅的后花园,仰躺在光挞挞的大青石上看书,觉得比在空调房里还舒服。 枕上读书这种方式,看上去闲散疏懒,所读之书,亦不过消遣尔尔,然回望之际,我发现自己居然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一年读完了五百本书,深感其堆金砌玉之妙。